 |
相關閱讀 |
【推薦】馮克利:利益馴化欲望,是資本主義的美德?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像“欲望”和“利益”這類概念,便是能夠引出大見識的小觀念。《欲望與利益》的副標題是“資本主義勝利之前的政治爭論”,由此可知它是一本有關資本主義早期觀念史的著作。 利益馴化欲望,是惡還是美德? 作者 | 馮克利 馬基雅維利在他落魄的晚年,曾給好友圭恰迪尼寫過一封著名的信,記述自己伏案寫作《君主論》和《論李維》的情形。白天他“四處游蕩,捉畫眉鳥,拾柴火,跟當地的粗人一起打牌,玩十五子棋”。傍晚回家后,他“脫掉臟兮兮的衣服和靴子,穿上宮廷的華服,與宮廷里的古人一起用餐……毫無羞澀地與他們交談,向他們請教他們的行為動機,他們也友善地回答我。這時我幾個時辰都不覺得無聊”。 據阿德爾曼說,畢生喜愛閱讀馬基雅維利的赫希曼,在寫作《欲望與利益》的過程中也像馬氏一樣,將自己沉浸在與古人對話之中。那時的赫希曼,在卡片上記滿了古人的名字和箴言,“與古代哲人一起追思舊邦……連他的衣著都讓人想起文藝復興時代的服裝。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大廳里,人們一眼就能認出既博學又衣冠楚楚的赫希曼”。 馬基雅維利緬懷舊事,是為了讓他的同胞重建羅馬人的榮譽意識,赫希曼回到古人中間,則是要喚醒今人對早期資本主義的記憶,恢復他們對其誕生的“奇跡感”。因為在他看來,那個時代的道德焦慮推動著對人性的反思,但人們通常都低估了它內生于傳統話語的程度。那是一個在既有的人性論內部發生緩慢變化的神奇過程。 其實,赫希曼本人的一生就是個很傳奇的故事。2012年底他去世后,《紐約客》專欄作家格萊德韋爾曾著長文《懷疑的才能》,講述了他不同尋常的經歷。 1915年赫希曼出生在柏林一個猶太富商之家,1933年入索邦巴黎大學,然后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最后是在意大利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這樣的教育背景足以使一個人有開闊的知識視野。而在學業之外,他的經歷更加不同尋常。西班牙內戰期間,他曾投身于共和派反抗佛朗哥的戰斗,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在法國馬賽大力營救過數千名猶太人,其中包括畫家杜尚、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和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加入美軍成了一名文官,在意大利參與過對納粹戰犯的審判。戰后他先是供職于美聯儲,參與過馬歇爾計劃的實施,然后在南美的哥倫比亞為世界銀行工作多年。當赫希曼真正轉向學術生涯時,已過不惑之年,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幾所精英大學和機構。他留下的著述并不很多,卻常有獨特的創見,以至有人認為,他沒有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是他的遺憾,而是諾貝爾獎委員會的錯誤。 確實,赫希曼通常被人視為一個杰出的發展經濟學家。他的《經濟發展戰略》和《退出、呼吁與忠誠》,使他在經濟學界享有盛譽。但赫希曼同時也是一個喜歡跨學科思考的人,現代森嚴的學科壁壘可以成為“專家”躲開質疑的避風港,但在赫希曼看來,卻是使人眼界狹窄的知識牢籠。所以我們看到,寫出《經濟發展戰略》的赫希曼,同時也是《欲望與利益》的作者,前者是典型的發展經濟學理論著作,后者則是對17和18世紀觀念史、甚至是修辭史的精深研究。它的主題雖然涉及經濟行為的動機,亦有對斯密和重農學派的討論,敘事方式卻完全回到了古典語境之中,調動的許多知識資源通常不會進入經濟學研究視野,例如培根、維柯、斯賓諾莎、孟德斯鳩和米勒等。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清晰看到赫希曼與哈耶克——他自20世紀40年代便喜歡閱讀的學者之一——的相似之處。第一,他們兩人都是不好歸屬于任何學科的思想家;其次,與哈耶克的無知理論相似,赫希曼認為,社會生活的復雜性給人類的認知能力設定了根本性的限制,但這種限制本身并不是一個不利因素,反而為人類以糾錯方式發揮創造力提供了廣闊空間,所謂發現無知要比已知更令人著迷,改進的動力也正是來源于此。這種思想在他寫于1967年的名篇“隱蔽之手原理”中有最集中的體現。 或許經歷過太多人世間的不測,他對那些以理性假設作為前提的理論推衍一向不以為然,更看重計劃的失敗為創新提供的機會:“創新的出現總是令我們驚奇,在它出現之前我們不可能想到它,甚至難以相信它是真的。換言之,我們不會有意識地從事這樣的任務,它所要求的創新我們事先就知道將會發生。我們能讓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的唯一方式,就是對任務性質的錯誤判斷。”無知確實能釀成惡果,但那多是因為政治領袖們的虛妄。他們宣稱擁有自己并不具備的整全知識并強力加以貫徹,結果是扼殺了個人根據變化作出調整的機會。 盡管赫希曼本人宣稱,《欲望與利益》一書與他過去的經濟學著作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我們從這本著作中仍可以看到以上思想方法的運用。他認為,新的觀念并不是從外部對抗舊既有體制中產生的,而是內生性危機因素的意外作用。《欲望與利益》導論中的一段話,可以視為這種認識方法的反映:“人們通常低估了新事物乃是源于舊事物的程度。將漫長的意識形態變化或演變描述為一個內生的過程,較之把它描述為獨立形成的反叛性意識形態與占主導地位的舊倫理的衰落同時興起,當然要更為復雜。”新思想的產生類似于一個應激性的進化過程,而應激源只能從它的機體內部去尋找。為描述這個過程的發生,就需要考察和辨別一系列相互關聯的觀念與主張,找出其源頭與變異的來龍去脈。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思想史,往往會發現一種新觀念的產生并不是來自周密的論證,而是一些存在于原有話語體系中的“小觀念”和“局部知識”,它們在意識形態中看似不占核心位置,更不能提供認識社會的整全知識,但是在某種社會變遷——本書中的例子是商業活動的增加——的刺激下,卻具有動搖既有意識形態的強大力量,能夠引起社會風尚的深刻變革。 此外,17和18世紀的思想者,與今天的理論家們最大的不同,大概是他們喜歡討論的不是“主義”,而是“人性”。翻一翻譬如洛克、亞當·斯密和孟德斯鳩的著作,我們便會發現,他們很少討論以“主義”冠名的各種思想,也不會把帶有“ism”后綴的詞作為核心概念。畢竟那時的西歐尚未進入“意識形態”時代,其世界觀仍是以自古典時代便已形成的各種人性論及其相關概念作為基礎。當然,這也是赫希曼能夠從修辭學的角度分析那個時代商業倫理的前提。 像“欲望”和“利益”這類概念,便是能夠引出大見識的小觀念。《欲望與利益》的副標題是“資本主義勝利之前的政治爭論”,由此可知它是一本有關資本主義早期觀念史的著作。為了尋找這些小觀念的影響,赫希曼必須冒險步入那個豐富而復雜的思想大廈,重建觀念序列而忽略其各種思想體系,這使此書更像是對17、18世紀思想生態的一次田野調查。那個時代發生過一場對商業行為的思想推銷運動,采用的方式之一,是通過對包含在“欲望”(passion)這個古老概念中的某些成分重新給予倫理學解釋,使人們從其負面價值的負担中解脫出來。 據赫希曼本人說,他這本書的構思,肇端于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的一句話: “幸運的是人們處在這樣的境況中,他們的欲望讓他們生出作惡的念頭,然而不這樣做才符合他們的利益。” 他由這個表述察覺到,對于人的“欲望”,自17世紀始,一些思想家開始從中區分出一種“利益”的成分,而在過去這樣的區分是不存在的。“欲望”中最突出的表現之一,即對財富的貪婪,一向被基督教認定為人類“七宗罪”之一,奧古斯丁將它同權力欲和性欲并列,稱為導致人類墮落的三大誘因。不過基督教神學的希臘化因素也給奧古斯丁的思考留下了烙印,他在譴責欲望的同時,還觀察到在不同的欲望之間存在著某種張力。比較而言,權力欲也許比另兩種欲望要好一些,它包含著追求“榮譽”和“公共美德”的傾向,可以抑制另一些罪惡。這雖然仍是一種古代世界的欲望觀,但它提示了欲望的不同成分是可以進行語義學操作的,這就為以后的“欲望制衡說”埋下了伏筆。 比如,就貪財這種欲望而言,如果決定某種行為是否有利可圖是來自經濟上的考慮,那么它是否應當被人廣泛接受,甚至應當得到贊美和推崇,則主要取決道德上的說服力。就像韋伯在解釋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的相關性時所說:賺錢的動機,經濟上的利己主義,是每個時代都常見的動機。正如中國有重農抑商的傳統一樣,它們在歐洲的基督教文明中,過去也僅僅是被人默默接受,而從不給予道德上的張揚。需要一項觀念上的重大轉變,才能把一種原來被視為人性中惡的因素,變為值得稱頌的美德。 一種發生在語言深處的變化,逐漸完成了這一使命。按赫希曼的分析,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基督教力主戴罪之人當以謙卑為上,文藝復興之際則出現了十分排斥利益考慮的“榮譽觀”和“英雄主義”。然而不知起于何時,這兩種價值觀開始同樣受到懷疑,一種為商業行為的新辯護誕生了。它既不像基督教的謙卑觀那樣壓抑欲望,也不像騎士的榮譽意識那樣放縱欲望,而是對欲望加以解剖,區別出它的不同功能。在赫希曼看來,最能代表這種思想轉變的,便是維柯下面這段話: 社會利用使全人類步入邪路的三種罪惡——殘暴、貪婪和野心——創造出了國防、商業和政治,由此帶來國家的強大、財富和智慧。社會利用這三種注定會把人類從地球上毀滅的大惡,引導出了公民的幸福。這個原理證明了天意的存在: 通過它那智慧的律令,專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們的欲望被轉化為公共秩序,使他們能夠生活在人類社會中。 這段話的意義在于,以往被認定為“人性之惡”的欲望,只要為它注入“智慧的律令”,便可以變為有益于人類福祉的力量。人類持有善惡觀或是一個常數,但何為善惡卻未必是一個常數,人作為一種能反思的動物,會隨著環境的變化對其進行調整。 這一調整的大背景是:文藝復興以后,尤其是17世紀以后,人們對于用道德教化或宗教戒律來約束人類欲望,已逐漸失去信心,于是他們開始尋找約束欲望的新方法。神的權威既已不足恃,重新解釋欲望本身的努力也就隨之產生。帕斯卡為贊揚人類的偉大而找出的理由是,人類“已經努力從欲念中梳理出了美妙的格局”和“美麗的秩序”。人的欲望是“有秩序的”,而在理性主義者眼中,秩序永遠是美麗的。它的美也許處于欲望者的意識之外,但就如同物質世界一樣,可以通過理性的分析對它加以認知甚至操控。 這種基于理性分析的思考,引發出許多非常著名的學說。培根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嚴肅地思考“如何讓一種欲望對抗另一種欲望,如何使它們相互牽制,正如我們用野獸來獵取野獸、用飛鷹來捕捉飛鳥”。斯賓諾莎更是直接斷言:“除非借助相反的更強烈的欲望,欲望無法得到限制或消除。”曼德維爾從欲望中區分出奢侈與懶惰,休謨則將貪財與貪圖安逸相對照,他們都認為,前者要比后者對社會更加有益。 然而有一個問題。這些見解不管從哲學角度聽起來多么動人,它能否落實為一種真正可以制服欲望的制度,仍是非常不確定的。按休謨的著名說法,理性很容易被欲望征服,成為它的奴隸。需要一種新的解釋方式,使欲望能夠與理性建立起可靠的聯系。完成這一解釋任務的關鍵,便是“利益”的概念。 赫希曼在“‘一般利益’和馴化欲望的‘利益’”這一節中,追溯了它的出現與詞義變化的過程。最初它是見于治國術中,羅昂公爵提出了“君主主宰臣民,利益主宰君主”一說。繼之又有愛爾維修對道德家的諷勸:“假如有人打算勸說輕佻的女人端莊而收斂,他應該利用她的虛榮心去克服她的輕佻,讓她明白端莊穩重是愛情和優雅享樂的來源……用利益的語言代替欲望有害的說教,他們便有可能成功地使人們接受其箴言。”另一位活躍在18世紀中葉政論舞臺上的英國主教巴特勒,則對利益和欲望的區別作了最清晰的表達: 特殊的欲望有悖于謹慎和合理的自愛,后者的目的是我們的世俗利益,一如它有悖于美德和信仰的原則;……這些特殊的欲望會誘發不利于我們世俗利益的魯莽行為,一如它會誘發惡行。 在傳統的道德說教失效的情況下,“利益”這個概念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它不是一個獨立于欲望和理性之外的概念,而是可以成為溝通和平衡兩者的橋梁:使欲望變成融入“理性”的欲望,使理性成為替“欲望”服務的理性。這種從利益的角度處理欲望的方式,促成了古老的人性論的一次制度主義轉折。由于人們認識到,欲望雖然無法克服,卻有可能使之向著利益的方向轉化,這不但“能更好地使之(欲望)得到滿足”,“在獲得財富方面有更大收獲”(休謨語),而且較之受單純欲望驅動的行為后果,它具有另一個明顯的優點:可以形成一種社會風尚,使貪婪在商業社會中變得有益無害。 正如斯密在《國民財富論》中所說,長期經商會使商人養成“長時間的勤勉、節約和小心經營”的習慣。曼德維爾在對比商業社會與古代的人格時,這一點說得更加清楚:“未開化者的……種種欲望更游移、更善變。在野蠻人身上,那些欲望比在有教養者身上更經常地相互沖突,爭占上風。有教養者受過良好的教育,已經學會了如何獲得個人安逸和生活舒適,如何為了自身利益而遵守規矩和法令,常能屈從較小的不便,以避免更大的不便。”當然,這種馴化欲望的利益也使理性不再那么潔凈,而是歸屬于算計利益的個人。然而正是有此一認識,才使得思想家們能夠闡述商業活動在敦化風俗方面發揮良好的作用,這在孟德斯鳩“哪里有商業,哪里就有良好的風俗”這類著名的說法中,得到了最好的表達。據赫希曼的考察,用利益去對抗其他欲望,以此推動社會進步,“這種思想已經變成了18世紀相當普遍的智力消遣”。 此外,它對政治生態也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商業利益的發展使統治者獲得了影響社會的巨大物質力量,后來的福利主義和帝國主義都可由此得到部分解釋;另一方面,它使統治者的濫權行為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其中作用最為明顯的,就是孟德斯鳩所大力贊揚的不動產的增長,它不同于土地這種傳統的財富形式,其易于流動性限制了君主的暴虐。孟德斯鳩認為,人類的權欲就像貪欲一樣,也是自我膨脹和不知饜足的,但利益的考慮同樣能夠使之得到馴化。他把當時流行的利益制衡欲望的觀點與他的權力制衡理論融合在一起,闡述了匯票和外匯套利可以成為“憲法性保障”的補充,充當對抗專制主義和“權力肆意妄為”的堡壘。用今天的話說,動產持有人可以用鈔票、甚至用腳投票,是使憲制得以形成的要素之一。 當然,欲望向利益的轉化并非沒有問題,在很多人看來它會讓世界變得“庸俗”,使人生“無趣”。更嚴重的是,它阻礙了“人類個性的充分發展”。馬克思的“異化說”,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都是對這種現象最著名的批判。對此,赫希曼以反諷的口氣說,這類指責恰恰表明,早期資本主義辯護家所取得的成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人遺忘了。 透過赫希曼還原的思想史場景可以看到,早期思想家對商業社會寄予希望,恰恰是因為“人性的充分發展”并不可取,而商業能夠“抑制人類的某些欲望和惡習,塑造一種不那么復雜和不可預測、更加‘單向度的’人格”。他們對欲望可能釋放出的能量有著強烈的道德憂慮,所以才將利益馴化欲望作為商業社會的偉大成就之一。而一個多世紀之后,這項成就卻被譴責為資本主義最惡劣的特征。 赫希曼在這本書中與斯密乃至韋伯一樣,同樣關注理性對資本主義行為合理化的作用,但他用更加具體鮮活的“利益觀”取代了韋伯的“新教倫理”。這一論證路徑的缺點是沒有解釋為何資本主義在一個地區得到接受的程度強于另一地區,好處則在于它為認識資本主義發生學提供了一個更加一般性的視角。我們也可以由此重新檢討一個被赫希曼一筆帶過,沒有深入討論的問題:現代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與以往歷史上的大規模征服有何不同? 赫希曼在全書結尾處談到資本主義帶來的“有益政治后果”時,引用了熊彼特的一個觀點:“一般說來,領土野心、殖民擴張的欲望和好戰精神并不像馬克思主義者所說,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避免的結果。倒不如說它們產生于殘存的前資本主義精神,然而不幸的是,這種精神在歐洲主要國家的統治集團中根深蒂固。”熊彼特并未涉及欲望和利益之分,但卻暗含著這樣一層意思:殖民擴張是源于赫希曼所說的“欲望”,而不是“利益”。在很多痛恨資本主義擴張的人看來,這種區分或許沒有意義,但忽略這種區分,可能也意味著看不到歷史上不斷發生的征服與資本主義擴張有何性質上的不同。 我們不必否認,資本主義為殖民擴張提供了強大的技術和物質手段。但這種征伐與擴張的原始動力,與其說是來自資本主義本身,不如說同奧斯曼帝國、蒙古帝國或西班牙帝國的前現代擴張方式的關系更為密切。就如赫希曼所說,在16世紀的西班牙人看來,“尊貴之人靠征戰獲得財富,要比卑賤之人靠勞動掙錢更光榮,更快捷”。當他們從“大征服”中崛起時,這成了他們特有的基本信念。換言之,它背后的動力是作為“欲望”之古典含義的貪婪,而不是受到現代商業社會推崇的“利益”。 不妨這么說,滿足欲望無法使人與動物相區分,獲取利益才是文明人的特征。所以,從赫希曼的分析來看,這種擴張與掠奪的現象,也只能視為一種前資本主義欲望的遺存,而不是來自“開明的自利”——工商業階層對“欲望”的一種獨特理解。這個團體也重視民族國家的建設,但是與過去的征服者不同,它的“利益觀”使它并不把國家的武力,而是把“溫和得體的商業活動”,視為獲取財富的主要手段。它最想直接獲得的不是金銀財寶,而是市場;它所建構的體制,也不同于近代之前的帝國體制,而是被差強人意地稱為“資本主義”。 本文選自阿爾伯特·赫希曼著、馮克利譯《欲望與利益》譯者序,轉載請注明來源。赫希曼傳奇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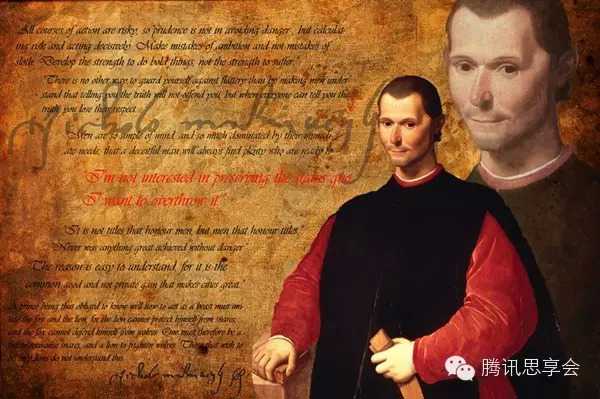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1469—1527),代表作《君主論》。從發展經濟學家到觀念史學家
 ▲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2012),學術研究涉及經濟學、政治學和思想史等多個領域。
▲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2012),學術研究涉及經濟學、政治學和思想史等多個領域。資本主義早期對“欲望”的新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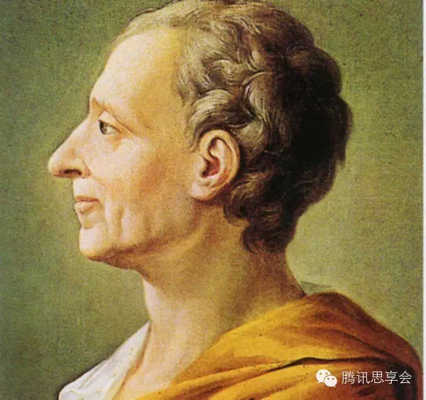
▲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法國啟蒙思想家,社會學家,是西方國家學說和法學理論的奠基人。道德或宗教在約束欲望時日漸失效
商業倫理興起:利益馴化欲望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的最新中譯本《欲望與利益》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與以往有何不同?
騰訊思享會 馮克利 2015-08-23 08:49:21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