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史景遷: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
 |
>>> 春秋茶館 - 古典韻味,時事評論,每天清新的思考 >>> | 簡體 傳統 |
原題:黑暗從內部升起
文/尹敏志
導語:史景遷在序言里寫道:“我所關注的卻是另外一些具體的個人,他們并不處于革命過程的最中心,卻以其特有的敏感描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苦痛。這些個人經驗有助于我們了解他們那個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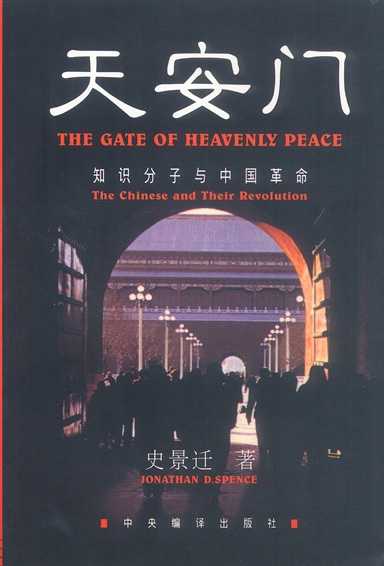
1
1920年夏,羅素(Bertrand Russell)費盡周折地到了蘇聯,并見到了列寧,卻失望地發現他智力平庸、性格狹隘,而且有一種“非同尋常的惡作劇般殘忍的氣質”。他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則是“封閉的暴虐的官僚體系,特務系統比沙皇時期更厲害更發達,貴族階層同樣冷漠和傲慢。”同年年底,羅素應梁啟超之邀來中國講學。待了一段時間后,他驚訝地發現,大部分中國人竟然對那個在他看來“極端恐怖”的國家充滿了幻想。
于是,在長沙名為《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的演講中,羅素憂慮地指出蘇聯這種以暴力奪取和維系政權、將無限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的共產主義是不可取的。
毛澤東恰好被《大公報》聘請為這場講演的特約記錄員,但這位湖南青年卻認為:羅素提倡的以教育實現共產主義的方法“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貧弱的中國沒有時間進行漸進改良,而迫切需要列寧所說的那種“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的革命。恐怖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獲勝的政黨“迫于必要,不得不憑借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
2
毛澤東的思想代表著中國革命在1920年代的一個重要轉變:革命的目的不再是為所有人爭取平等的權利;而僅僅是為其中一部分人,即“無產階級”爭取權利, 留給剩下的那些“階級敵人”的將是殘酷的“無產階級專政”。這種訴諸仇恨的馬列主義是進行武裝斗爭時的利器,但其危險性在于:劃分這兩種人的界限是模糊的,很多時候甚至僅僅取決于領袖的個人意志。因而,這就為日后從內部升起的黑暗埋下了伏筆。
按黑格爾(G. W. F. Hegel)的說法——馬克思的觀點與之相近——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革命領導人是 “世界精神”的代言人,他們能夠將潛在的、不自覺的歷史必然性帶到自覺的實踐。至于大部分民眾,對歷史而言都是無關緊要的,他們能做的僅僅是“追隨這些靈魂領導者,因為他們感受著他們自己內在的精神不可抗拒的力量”。
但史景遷(J. D. Spence) 的《天安門: 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似乎故意要與這種史觀相悖:僅僅關注革命領導人是不夠的;有時候,反而是那些革命邊緣人的經歷,更有助于勾勒出革命真正的面貌。史景遷在序言里寫道:“我所關注的卻是另外一些具體的個人,他們并不處于革命過程的最中心,卻以其特有的敏感描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苦痛。這些個人經驗有助于我們了解他們那個時代。”
3
《天安門》是以康有為、梁啟超坐蒸汽船赴京趕考的途中,在中國海上遭遇到了日本軍艦的攔截和搜查開始的。同一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悲憤交加的康梁率領數千民上京趕考的舉人聯名上書,反對條約,拉開了變法維新的序幕。
雖然痛恨日本的侵略, 但康有為變法的根本思想卻是來自明治維新。在他看來:在外有居心叵測的列強虎視眈眈,內有愚弱的、根本不知民主為何物的國民的情況下,最好是像日本一樣,由一個強有力的威權政府來推動自上而下的變革,實行君主立憲。一面抵御外侮,一面教化民眾。
不可否認, 從今天看來, 康有為提出的主張自有其合理之處。在中國傳統中,皇帝扮演的一直是政教合一的角色。民眾對皇帝的依賴性非常強。所以,即使在制度上將皇帝廢立了,兩千多年的王朝專制在民眾內心留下的奴性卻無法泯滅,他們無比渴望一個新的全能領袖的出現。尤其是在長久的動亂后,一旦有一個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合一的類“圣王”,他們會立即匍匐于其腳下,高呼紅太陽。
由于操之過急, 維新變法引起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彈。變法失敗后康有為逃到國外,在日本,孫中山想要見他,卻被拒絕了——康不屑與孫這種革命黨為伍,“虛君共和” 才是其一貫主張。康堅持認為,革命只有可能在像美國和英國那樣有悠久的民主傳統的國家成功。而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除了將兩千多年的專制沉淀重新翻攪起來以外,革命還能做什么?但戊戌變法后,立憲派實際上大勢已去,革命派則越來越得勢。
孫中山始終記得當年康有為對他的怠慢。作為報復,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他就派人拆了立憲派在日本的會所。梁啟超在一封信里描述當日情景:“所有什物相架門口匾額對聯全行拆廢,拋之街外,有中立人見而不平,公論一兩句,則被他黨人隨街驅逐毆打,曾打四五人不堪者,幸各同志知機,無與其爭論,故無損傷者,然亦受辱不少矣。”信的末尾,梁近乎詛咒地寫道:“真是強橫無禮,禽獸之不若也。俗云所謂‘未登天子位,先置殺人刀’,天必不佑,且觀其后矣。”
梁啟超的預言最后成了現實。我們可以從孫中山那里看到中國幾乎所有革命者身上普遍的矛盾之處:在紙面上,或未成功前,他們滿口是民主、憲政、自由;但是,一旦進入實際操作階段,專制、獨裁、黨同伐異等各種傳統的陰暗手段又會被同一個人熟練地調用出來。這種轉變往往是不自覺的。
這種言行不一更深層的原因是革命者們確信“目的證明手段合理”:只要理想是崇高的,那現實中的任何殘忍和黑暗都是可以被忽略的——瞿秋白在蘇聯期間,親眼見到了在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下,饑餓的農民煮食尸體,或者絕望地點燃房屋燒死自己,但這都沒有動搖他的信仰。瞿秋白并非冷酷無情,而是在他看來這些手段與“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并不沖突:“為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著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一定要先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覺得很有趣。”
正是在這種“目的證明手段合理”的信念中,原本志在推倒一切的革命者們,欣然重拾那些被早已被唾棄的舊東西,并逐漸蛻變成當初自己要打倒的人。托克維爾(A.Tocqueville)研究法國革命后得出的結論也完全適用于中國。他發現,在革命過后,“取勝的是舊制度的那些原則,它們當時全部恢復實施,并且固定下來。”“恰如某些河流沉沒地下,又在不太遠的地方重新冒頭,使人們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魯迅卻認為,革命失敗的責任不該歸咎于革命者。1907年,他在日本寫出《摩羅詩力說》,熱情地呼喚道:“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于善健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可是二十多年后,他絕望了。因為即使這樣的戰士出現,等待他的命運也無非是“叫人叫不著,自己頂石墳”,“然而市民是這樣的市民,黎明也好,黃昏也好,革命者們總不能不背著這一伙市民進行。雞肋,棄之不甘,食之無味,就要這樣地牽纏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無把握的。”
到底是“革命”還是“不革命”?魯迅終其一生都被這個問題所折磨。有時候他認為,革命這個手段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可另外一些時候,他又不禁從根本上懷疑起這一切:“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系的,因為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
丁玲的立場不像魯迅那么猶疑不定。她始終信仰共產主義革命,這一趨勢在丈夫胡也頻被國民黨槍殺后更加明顯。在被軟禁3年多后,她于1936年輾轉逃到了中央蘇區,這位著名作家受到了中共的熱烈歡迎,毛澤東甚至親自接見了她。雖然延安的條件很艱苦,但她卻在那里如魚得水。
可是漸漸地,她發現延安存在著嚴重的“首長至上”現象,上下尊卑等級鮮明;作家只被當做宣傳工具使用,沒有任何創作自由;甚至連戀愛都是受限的,只能由領導介紹批準。1942年3月,為響應毛澤東鼓勵黨外人員“善意的批評”的號召,丁玲寫出了《三八節有感》一文,并在自己主編的《解放日報》刊出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
沒想到,這些文章引得龍顏震怒,“發揚民主作風”很快變成了打擊“自由化”。幸好丁玲在國統區的名氣大,得到的處罚只是被下放至北大荒兩年而已。作為替罪羊,可憐的無名小卒王實味則被殘酷批斗,不久被逮捕,從此失去人生自由。即使他無數次痛哭流涕地懺悔,寫了無數交代材料,1947年還是在山西被康生下令砍了頭。
4
韋伯(Max Weber)曾說過:“打算用武力在地球上建立絕對正義的人,他需要有追隨者,有一架由人構成的‘機器’。他得不斷為這些人提供精神的和物質的必要獎賞……領袖的實際收獲,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隨者的動機所左右,而從道德角度看,這些動機大都不堪聞問。”
一般來說,革命機器的組織及意識形態控制越嚴密、領導人越權威、等級制越鮮明,效率就越高,奪取政權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也越傾向于專制獨裁;而另一方面,革命組織內部越崇尚平等、成員行動越自由、意識形態統治力越弱,那革命機器就越松散無力,因而更可能被鎮壓或淘汰——這是所有革命內部難以解決的一個永恒悖論。如何在保持戰斗力和控制內部黑暗因素之間保持平衡,是擺在革命面前的最棘手問題,其難度不亞于走鋼絲。實際上,除了少數特例,所有暴力革命基本都失敗了。革命的目標定得越高,意味著對人性幽暗面的警惕越低,那么,它就越可能走向失控和暴虐,甚至可能反過來吞噬那些目標純潔的革命者。
5
雖然丁玲經過延安整風后,對黨無疑更加忠誠了,但她仍然在“反右” 時期被打成“文藝界的大右派”,再次被下放北大荒12年。1970年,文革小組找到了她,丁玲以為他們是來救自己的,沒想到反而被關進了條件更為惡劣的單人牢房里。其后整整5年,她被毆打、虐待,所有親友都被禁止探監,她陷入徹底的孤獨之中。
直到1978年,丁玲才真正重獲自由。但幾乎與此同時,一個30歲的年輕電工因為在西單民主墻上寫下“人民還在被封建思想所愚弄,還在被封建的枷鎖束縛著”的句子而被判十多年重刑。
書的結尾,史景遷問道,漫長的革命真的讓中國人 “為自己和自己的國家爭取到了那些在一個世紀里一再被允諾,卻從未被實現的東西嗎?”答案是否定的。和一百年前比,革命帶來的最大變化,恐怕就是革命話語的“名”與“實”被完全顛倒過來了:最恐懼革命的人完全壟斷了“革命”的使用權,聲稱與他們相對就是與革命相對。而用一百年前的眼光看來無疑是“革命者” 的人, 現在卻成了“ 反革命”。
來源: 經濟觀察報 | 來源日期:2011-10-26
民國的資料比較麻煩,因為當時沒能建立一個組織,國民黨沒有贏,軍閥沒有贏,共產黨的勝利某種意義上
是由于其他人的失敗。這也是我《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該書由康有為、魯迅、丁玲三個人延
伸出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的情況)一書的主題。
網載 2015-09-26 21:22:31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