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流沙河 鋸齒嚙痕錄 自傳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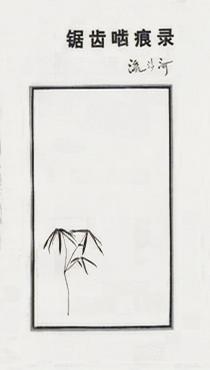
自傳
1931年11月11日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忠烈祠南街一個小院里。我的老家在距離 成都市八十八華里的金堂縣城廂鎮(該鎮今屬成都市青白江區了)槐樹街余家大院 內,原是一個大地主家庭。我三歲那年隨父母遷回老家的時候,家道早已式微,父 輩們分了家,各自揮霍殆盡。我的父親余營成這一房有田二十畝,算是小地主。
父親余營成1920年求學北京,學業不佳,酷愛京戲。書未讀完,回成都經商, 折本歇業,入四川法政學堂。就學期間娶了我的母親劉可芬。母親劉可芬,四川省 雙流縣鄉下人,其家庭系地主,被其繼母拐騙來成都,說與我的父親做了二房。其 繼母欺騙我的外祖父,詭稱我的母親已在成都病死,并在郊外的青羊宮附近造假墳 一座,說就埋葬在此。母親向父親哭訴了被拐賣的經過情形,父親便向法院起訴。 真相大白,可憐的外祖父找到了“死去的”女兒,相對大哭。此案詳情刊載在當時 (二十年代)成都的一張報紙上。遺憾的是木已成舟,母親已嫁給父親了,外祖父 只好承認這一門婚姻。父親待母親好,教她識字,后來母親就能春節寫信了。母親 至今健在。父親曾在國民黨金堂縣政府任職軍事科長,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民憤甚 大,被處死刑。這是應該的。
我是母親的長子,備受寵愛。槐樹街余家按大排行計算,我是同輩中的第九, 所以小名老九,又名九娃子,而我的本名是余勛坦。自幼體弱多病,怯生,赧顏, 口吃。兩歲以前在母親的麻將脾上已識“中”字,這是我認得的第一個漢字。四歲 已認完一盒字方(正面是字,背面是圖,看圖識字),都是母親教的。
1938年入學。先讀縣城里的女子小學(因為怕挨男同學的打),后轉讀金淵小 學。讀小學畢業班的那年,自學李煜的詞,尤愛《夢江南》《虞美人》兩首,這是 學舊體詩詞之始。同時開始學做文言文,無非是“夫人生天地之間……”“何以言 之?”“豈不痛哉!”那一套。1944年入金堂私立崇正中學。每周一篇作文,做文 言文。春天做《春郊游記》,秋天做《觀刈禾記》,端午節來了,做《觀龍舟競渡 記》,天寒了,做《說冬日之可愛》。學了賈誼的《過秦論》,做《過秦論書后》, 學了司馬遷的《李斯傳》,做《論李斯》。美國總統羅斯福逝世了,做《悼羅斯福》 ——這篇作文我得一百分。老師在課堂上朗讀此文,萌醒了我最初的發表欲。出題 做文,都有舊規陳套,全是八股翻新。國文老師只選講《古文觀止》《經史百家雜 鈔》,不采用國民黨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文言文結構謹嚴,條理分明,極少廢話, 對我日后從事文字工作大有好處。除了在校攻讀文言文而外,每日課余及每年寒暑 假,我還得就學于一位貧窮而善良的老秀才黃捷三先生,聽他逐字逐句他講解《詩 經》《論語》《左傳》《唐詩三百首》《千家詩》。還自學了一本《聲律啟蒙》, 這真是一本奇書!“云對南,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 尺劍,六鉤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官。兩岸曉煙楊柳綠,一簾春 雨杏花紅……”低吟緩誦之際,但覺音韻鏗鏘,詞藻華麗,妙不可言,很自然地領 會了平仄對仗。當時以為懂得平仄對仗,就能做舊體詩了,便偷偷寫了一些可笑的 五言六言。老家門前有五株古槐,晨昏鴉噪,夜半梟啼,炎夏濃蔭,寒秋落葉,為 我提供了最初的詩材,當然都是無病呻吟,“為賦新詞強說愁”的了。那時候我夢 想做一個詩人,認為抒發感情乃是一件高尚而又有趣的事情。至于“歌詩合為時而 作”的起碼道理,當時是根本不知道的,當然更想不到一吟一詠如果不合時宜竟會 給自己帶來窮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辭》注釋家蔣驥說:“騷憂乃不祥之書也!” 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懂得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也是1944年我剛入中學的時候,讀到了第一首印象最深、至今尚能背涌的新詩, 那就是我們四川詩人吳芳吉在五四運動前一年寫的《婉容詞》。這首敘事詩說的是 一位受封建禮教三從四德束縛的弱女子,名叫婉容,賢淑美麗,被其留學美國的鍍 金博士丈夫所遺棄,幾番感傷徘徊之后,投江自殺。寫得哀婉凄切,一吟三嘆,讀 之淚下。此詩在語言音韻方面兼有舊體詩詞之長,如新蟬自舊蛻中羽化而出,似舊 而又非舊,一鳴驚人,風靡全川,對我影響很深。
1947年春季離開老家,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學(高中部)。那正是國統區進步學 生運動如火燎原的年代,罷課抗議,游行示威,風起云涌,我卷入其中。一位姓雷 的同學領著我們上街游行,到省政府門前呼口號:“打倒王陵基!”我們唱著兩支 紅色的歌,一支是《團結就是力量》,一支是《山那邊,好地方》,意氣昂揚,心 向延安。順便說一句,這位姓雷的同學在解放前夕被國民黨逮捕,險遭殺害,得救 出獄,在六十年代做了我的故鄉金堂縣縣委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虐不堪, 自殺身死了。后話不提,書歸正傳。當時我無心讀書于課堂,有意探求于文學,狂 熱地閱讀巴金的小說、魯迅的雜文、曹禺的戲劇,特別是艾青、田間、綠原的詩, 抄錄了厚厚的一本,認為《向太陽》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首詩,而唐詩宋詞被我 棄之如敝履。我已經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叛逆者了。
也是1947年早春我剛入高中的時候,重慶《新華日報》駐成都辦事處被迫撤回 延安的前夕,該辦事處的書店公開散發書籍。我聞汛急往,得一本蕭三著《毛澤東 的少年時代》,如獲至寶而歸。如今物換星移人漸老,每次經過祠堂街的時候,還 要注目留情于那家書店的舊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當時成都有一家進步的《西方日報》,報社里有好些地下黨的同志在工作。1948 年秋季我向該報投稿,報道校園生活,多次刊用。在該報副刊上發表了我的第一個 短篇小說《折扣》,側寫一位老師的困苦生活。說來慚愧,構思借自二十年代女作 家黃廬隱的一個短篇小說,只能算是模擬之作。作品排成鉛字,受到鼓舞,此后便 有志做一個作家了。于是又讀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的小說,還讀蘇聯小說《鐵流》 《夏伯陽》《靜靜的頓河》《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還讀美國小說《飄》, 而對新詩的興趣大減。這年還惹過一點小小的麻煩。在《西方日報》上寫消息揭露 學校生活的污糟,激怒了以姓涂的為首的幾個三青團學生,聯名貼大字報威嚇我, 叫我出來答辯。幸以筆名發表,不知是我寫的,得免罹禍。我膽小,再不敢亂寫了。
1949年春季,在成都的《青年文藝》月刊上發表短篇小說《街頭巷尾》,因而 加入青年文藝社,該社成員多系成都的中學生文學愛好者。同時在成都的《新民報》 《西方日報》上發表短篇小說、詩、譯詩、雜文共十多篇。這年秋季以高中五期學 歷跳考四川大學農業化學系,以該系第一名的優良成績被錄取。入學后不想去聽課, 只寫東西。年底,喜迎成都解放。
成都解放后,此時已入1950年了,我想做作家,不愿返校求學,也不愿參軍到 文工團(紀律太嚴)。于是回到故鄉金堂縣城,在縣學生聯合會協助宣傳工作。后 來又到金堂縣淮口鎮女子小學教書,近一個月。那時候自學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 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眼界頓開,立即照辦,為了“和工農兵打成一片”,志愿上 山去教村小。二十多天以后,因已在《川西日報》副刊上發表過演唱作品和短篇小 說,引起了該副刊主編西戎同志(當時他是青年作家)的注意,在素昧生平的情況 下,蒙他信任,來信約我去報社參加工作(當時都說參加革命)。我便結束了五十 天教師生活,到西戎那里報到去了。看見我不是他所估計的一個老頭兒而是一個小 青年,他很滿意,一直對我極好。1951年,我編《川西農民報》副刊版兼時事版, 同時發表了許多演唱宣傳品,工作很努力。還發表了與別人合寫的中篇小說《牛角 灣》。該小說有嚴重缺點,在黨報上受到十多篇文章的嚴厲的有益的但是未必中肯 的批判。由于有西戎關照,只批判到“企圖以小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現實”, “將導致亡國亡黨”為止,沒有再加碼,沒有把我當敵人看待。寫了一篇檢討文章 公開發表,松松活活地我就過關了。
西戎不擺官架子與文架子,平易近人,帶我下鄉體驗生活,與我合寫東西,鼓 勵我,批評我,使我獲益不淺,終身難忘。在隨后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我勇于批判 自己的舊觀念,并在思想上與地主階級劃清界限,努力樹立革命的人生觀,覺得自 己大有進步,于1952年5月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不久以后,調至四川省文 聯工作,做創作員,發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說、評論文章。
1953年我到大邑縣三岔鄉第七村體驗生活,住村長家中,目睹土地改革后農村 的太平富庶與農民的快樂勤勞,至今不忘。在那里寫中篇小說與劇本,都不成功。 這年秋天又轉移到新繁縣禾登鄉新民社體驗生活,住社長家中。第二年又在這里做 普選工作,做糧食統購工作,同時寫一些東西,也都不成功。原因是自己缺少求實 精神,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激烈斗爭”的套子去套量生活,主觀主 義地從概念出發,緣著教條瞎編故事,這樣還能寫出象樣的東西來嗎!后來回省文 聯到《四川群眾》做編輯工作,發表幾個短篇小說,其中《窗》一篇稍好。當時我 讀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小說入迷,深受其影響。在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運動 中,我也寫了兩篇文章發表,無非是順大流唱通調而已,毫無學術價值可言。1955 年在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運動中,我也寫文章發表,并寫宣講提綱,多有強詞奪理 之處,歪曲了人家的本意,然后又把人家臭罵一頓。在此謹向胡風同志致歉!
這年寫詩《寄黃河》發表后稍有好評,乃努力寫詩。寫組詩《在一個社里》發 表后又稍有好評,便寫詩愈勤。此后才走上了寫詩的軌道,仍做創作員。幾個月湊 夠了一本,交給重慶人民出版社。第二年即1956年出版了,書名《農村夜曲》,現 在讀了很慚愧。
1956年早春去北京出席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眼界大開,詩思大涌。會后 被中國作家協會安排去采訪先進生產者,并列席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會后又 求學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三期),那是一個大出人才的學習斑。美麗的北 京給我以豐富的感情燃料,覺得到處都有詩。八個月里寫了許多小詩,又湊夠了一 本,交給作家出版社。第二年即1957年春天我的《草木篇》剛剛被批判以后出版了, 書名《告別火星》,現在讀了有些慚愧。1956年還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過一本短 篇小說集《窗》,其中只有《窗》一篇和《辣椒與蜜糖》一篇稍好。
1956年秋天在文學講習所結業后,心情悒郁,回四川去,在南行的列車上寫了 題名《草木篇》的五首小詩。回去不久,我參加了《星星》詩歌月刊的籌備工作。 “星星”這個名字是丘原同志取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身死于監獄了,愿 他靈魂快樂!《星星》編輯部只有四個編輯:白航(主編),石天河(執行編輯), 白峽(編輯),流沙河(編輯),即“二白二河”,反右派運動中無一幸免。一個 編輯部弄得全軍覆沒,象《星星》這樣的下場,海內僅此一家,再無二例!
1957年元月,《星星》創刊號面世十四天以后,在《四川日報》上受到可怕的 指責,罪名是假“百花齊放”之名,行“死鼠亂拋”之實。發表在創刊號上的《草 木篇》,本來是微不足道的東西,也招來了省市兩報大規模地猛烈地轟擊,使我驚 訝。批判愈演愈烈,升級到“反革命”與“階級仇恨”的高度,海內為之側目。我 想不通,抗辯,發言見報,徒自取辱而已,有個什么用呢!后來許多人(幾乎都是 從未晤面的)為此受牽連,遭遇很慘。
被錯劃為右派后,誠惶誠恐,“認罪”尚好,幸獲寬大,開除共青團,開除公 職,留在省文聯機關內監督勞動,掃地,燒水,拉車,到崇慶縣山中去煉鐵,混完 了1958年。其間寫了一個長詩《三人行》,三千行,稿本被收去了,不知下落。勞 動之余,潛心研讀《莊子》,記得爛熟。1958年被叫到省文聯的《草地》編輯部打 雜,登記來稿,修改刊用稿,盡心悉力,為時一年。工余研讀《詩經》《易經》 《屈賦》。1960年被叫到省文聯的農場開荒種菜。病水腫,叫回機關休息,便研讀 摩爾根《古代社會》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961年被叫到省文 聯的已停工的建筑場地種菜,夜夜守菜園,專抓偷菜者。由于克盡厥職,過分積極, 反被偷菜者打了一頓,還被扭送派出所,哭笑不得。1962年被叫到省文聯的圖書資 料室協助工作,利用方便條件,閱讀大量古籍。我一貫愛讀書,相信開卷有益,三 教九流,來者不拒。被孤立了,無人同我往來,免除干擾,正中下懷。不回寢室睡 覺,在圖書室里夜以繼日地狼吞虎咽地讀,在沙發椅上過夜。先是研究古代天文學, 從此成為一個興趣歷久不衰的天文愛好者。后來搜集有關曹雪芹的資料,寫出敘事 詩《曹雪芹》,五百行,稿本在后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焚毀。
從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為止,八九年間,利用勞動之余暇,我 研讀了四書五經、先秦諸子、中國古代史、民俗學、古人類學、唐宋明三代的野史 筆記、古代天文學、現代天文學,做了大量的摘錄與索引,寫了許多心得,都是寫 在廢紙背面的。我對古漢字學最有興趣,鉆透了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做了上 十萬字的筆記,并在此基礎上完成一部頗具趣味性的解說古漢字的普及讀物,花了 我三年的時間。此稿題名《字海漫游》,約八萬字,被紅衛兵搶走,終不可尋。悵 悵!
1966年春天,黑茫茫的長夜來臨了,我被押解回故鄉金堂縣城廂鎮監督勞動改 造,此后全靠體力勞動計件收入糊口了。這年的七夕我結婚了。接著來的是抄家、 游斗、戴高帽。成都的紅衛兵來抓我,意欲弄我回成都去批斗。幸好本縣某領導人 及時將我潛移鄉下三日,躲過了一場可能被打傷致殘的橫禍。那些領導人,包括本 鎮派出所所長,都是嚴肅認真地按照當時的政策對待我的,沒有給我以額外的難堪 的折磨,我至今對他們毫無怨尤。他們都是好人,可惜后來很快地就被人家打倒了 或靠邊站了。
我在故鄉勞動十二年,前六年拉大鋸,后六年釘包裝箱,失去任何庇蔭,全靠 出賣體力勞動換回口糧維系生命,兩次大病,差點嗚呼哀哉。后六年間,壓迫稍松, 勞動之余暇,溫習英語,為小兒子編寫英語課本十冊,譯美國中篇小說《混血兒》, 通讀《史記》三遍,寫長詩《秦火》,一千行,此稿自毀了。在那十二年的長夜中, 只留下《情詩六首》《故園九詠》兩組小詩和《喚兒起床》《故鄉吟》等幾首小詩, 實在慚愧!另外,香港某出版公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照相翻印出版我的詩集 《告別火星》發賣,乃屬盜印,我完全不知道。
二十二年的艱難日月給了我有益的鍛煉。我一直朦朧地眺望著未來的光明,不 怨天尤人,不自暴自棄,努力求學,正派做人,相信將來還有為人民服務之日。惜 乎頭發漸漸花白,歲月不我待了。保爾·柯察金說得好:“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 的多。”回顧自己的大半生,我是滿意的,我值得。
江青反革命集團落網后,我很快活,背負著生病的小兒子上街看大標語,教他 認標語上的大字。我的妻子從外地歸來,她也很快活。我說:“從今以后,我可以 拚命地釘包裝箱了。”她說:“我用不著東躲西藏了,我可以去收破爛維持生活 了。”我們所求甚微,只望國家安定,個人能夠勞動謀生,便是萬幸了。
1978年5月在故鄉我被宣布摘帽,年底被調到縣文化館工作。三中全會后,天 大亮了,我才真正蘇醒了,想起我曾經是一個詩人,也許還能寫幾句的,于是技癢 了。1979年4月,在沉寂二十二年之后,首次在《詩刊》上發表《詩二首》。這該 感謝《詩刊》的編輯同志,是他們叫醒了昏沉沉的我。7月,《人民日報》又發表 了我的《梅花戀》,《成都日報》又發表了我的《帶血的啼鵑》,都給了我很大的 幫助。9月,由中共四川省委下達正式文件,為1957年的《星星》詩歌月刊平反, 為包括我在內的四個編輯平反,也為《草木篇》平反。至此,我被錯劃為右派的結 論才得到改正。10月,《星星》復刊,我被調回原單位四川省文聯,仍在《星星》 做一名普通的編輯人員。
1980年我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1981年我加入了研究飛碟現象的中國UFO四川 分會。我的組詩《故園六詠》有幸獲得1979-1980年全國中青年新詩獎。謝謝。
1981年7耳24日在成都寫定
流沙河 2013-08-22 13:10:38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