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布羅茨基《悲傷與理智》 一日一書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悲傷與理智 作者: [美] 約瑟夫·布羅茨基 劉文飛譯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15-4 首先,在藝術與現實的關系問題上,布羅茨基斷言:“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時而大于現實”(《戰利品》)。他認為,不是藝術在模仿現實,而是現實在模仿藝術,因為藝術自身便構成一種更真實、更理想、更完美的現實。“另一方面,藝術并不模仿生活,卻能影響生活。”(《悲傷與理智》)“因為文學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釋各種人類命運、各種體驗之含義的手冊。”(《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他在他作為美國桂冠詩人而作的一次演講中聲稱:“詩歌不是一種娛樂方式,就某種意義而言甚至不是一種藝術形式,而是我們的人類學和遺傳學目的,是我們的語言學和進化論燈塔。”(《一個不溫和的建議》)閱讀詩歌,也就是接受文學的熏陶和感化作用,這能使人遠離俗套走向創造,遠離同一走向個性,遠離惡走向善,因此,詩就是人類保存個性的最佳手段,“是社會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險形式;它是一種針對狗咬狗原則的解毒劑;它提供一種最好的論據,可以用來質疑恐嚇民眾的各種說詞,這僅僅是因為,人的豐富多樣就是文學的全部內容,也是它的存在意義”(《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與一個沒讀過狄更斯的人相比,一個讀過狄更斯的人就更難因為任何一種思想學說而向自己的同類開槍”(《表情獨特的臉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羅茨基在本書中不止一次地引用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命題,即“美將拯救世界”,也不止一次地重申了他自己的一個著名命題,即“美學為倫理學之母”。布羅茨基在接受諾貝爾獎時所做的演說《表情獨特的臉龐》是其美學立場的集中表述,演說中的這段話又集中地體現了他的關于藝術及其實質和功能的看法: 就人類學的意義而言,我再重復一遍,人首先是一種美學的生物,其次才是倫理的生物。因此,藝術,其中包括文學,并非人類發展的副產品,而恰恰相反,人類才是藝術的副產品。如果說有什么東西使我們有別于動物王國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語言,也就是文學,其中包括詩歌,詩歌作為語言的最高形式,說句唐突一點的話,它就是我們整個物種的目標。 一位研究者指出:“約瑟夫•布羅茨基創作中的重要組成即散文體文學批評。盡管布羅茨基本人視詩歌為人類的最高成就(也大大高于散文),可他的文學批評,就像他在歸納茨維塔耶娃的散文時所說的那樣,卻是他關于語言本質的思考之繼續發展。”關于語言,首先是關于詩歌語言之本質、關于詩人與語言之關系的理解,的確構成了布羅茨基詩歌“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他將詩歌視為語言的最高存在形式,由此而來,他便將詩人置于一個崇高的位置。他曾稱曼德施塔姆為“文明的孩子”,并多次復述曼德施塔姆關于詩歌就是“對世界文化的眷戀”的名言,因為語言就是文明的載體,是人類創造中唯一不朽的東西,圖書館比國家更強大,帝國不是依靠軍隊而是依靠語言來維系的,而詩歌作為語言之最緊密、最合理、最持久的組合形式,無疑是傳遞文明的最佳工具,而詩人的使命就是用語言訴諸記憶,進而戰勝時間和死亡、空間和遺忘,為人類文明的積淀和留存作出貢獻。但另一方面,布羅茨基又繼承詩歌史上傳統的靈感說,夸大詩人在寫作過程中的被動性,他在不同的地方一次次地提醒我們:詩人是語言的工具。“是語言在使用人類,而不是相反。語言自非人類真理和從屬性的王國流入人類世界,最終發出這種無生命物質的聲音,而詩歌只是其不時發出的潺潺水聲之記錄。”(《關愛無生命者》)“實際上,繆斯即嫁了人的‘語言’”,“換句話說,繆斯就是語言的聲音;一位詩人實際傾聽的東西,那真的向他口授出下一行詩句的東西,就是語言。”(《第二自我》)布羅茨基的諾貝爾獎演說是以這樣一段話作為結束的: 寫詩的人寫詩,首先是因為,詩的寫作是意識、思維和對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個人若有一次體驗到這種加速,他就不再會拒絕重復這種體驗,他就會落入對這一過程的依賴,就像落進對麻醉劑或烈酒的依賴一樣。一個處于對語言的這種依賴狀態的人,我認為,就可以稱之為詩人。 最后,從布羅茨基在《悲傷與理智》一書中對于具體的詩人和詩作的解讀和評價中,也不難感覺出他對某一類型的詩人及其詩作的心儀和推崇。站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講壇上,布羅茨基心懷感激地提到了他認為比他更有資格站在那里的五位詩人,即曼德施塔姆、茨維塔耶娃、弗羅斯特、阿赫馬托娃和奧登。在文集《小于一》中,成為他專文論述對象的詩人依次是阿赫馬托娃、卡瓦菲斯、蒙塔萊、曼德施塔姆、沃爾科特、茨維塔耶娃和奧登等七人。在《悲傷與理智》一書中,他用心追憶、著力論述的詩人共有五位,即弗羅斯特、哈代、里爾克、賀拉斯和斯彭德。這樣一份詩人名單,大約就是布羅茨基心目中的大詩人名單了,甚至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詩歌史。在《悲傷與理智》一書中,布羅茨基對弗羅斯特、哈代和里爾克展開長篇大論,關于這三位詩人某一首詩或某幾首詩作的解讀竟然長達數十頁,洋洋數萬言,這三篇文章加起來便占據了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布羅茨基在文中不止一次提醒聽眾,他在對這些詩作進行“逐行”解讀:“我們將逐行分析這些詩,目的不僅是激起你們對這位詩人的興趣,同時也為了讓你們看清在寫作中出現的一個選擇過程,這一過程堪比《物種起源》里描述的那個相似過程,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我還要說它比后者還要出色,即便僅僅因為后者的最終結果就是我們,而非哈代先生的詩作。”(《求愛于無生命者》)。他在課堂上講解弗羅斯特的詩時,建議學生們“特別留意詩中的每一個字母和每一個停頓”(《悲傷與理智》)。他稱贊里爾克德語詩的英譯者利什曼,因為后者的譯詩“賦予此詩一種令英語讀者感到親近的格律形式,使他們能更加自信地逐行欣賞原作者的成就”(《九十年之后》)。其實,布羅茨基不止于“逐行”分析,他在很多情況下都在“逐字地”、甚至“逐字母地”地解剖原作。他這樣不厭其煩,精雕細琢,當然是為了教會人們懂詩,懂得詩歌的奧妙,當然是為了像達爾文試圖探清人類的進化過程那樣來探清一首詩或一位詩人的“進化過程”,但與此同時他似乎也在告訴他的讀者,他心目中的最佳詩人和最佳詩歌究竟是什么樣的。布羅茨基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學生后來在回憶他這位文學老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布羅茨基并不迷戀對詩歌文本的結構分析,我們的大學當時因這種結構分析而著稱,托多羅夫和克里斯蒂娜常常從法國來我們這里講課。布羅茨基的方法卻相當傳統:他希望讓學生理解一首詩的所有原創性、隱喻結構的深度、歷史和文學語境的豐富,更為重要的是,他試圖揭示寫作此詩的那門語言所蘊藏的創作潛力。”在關于弗羅斯特《家葬》一詩的分析中,布羅茨基給出了全文、乃至全書具有點題性質的一段話: 那么,他在他這首非常個性化的詩中想要探求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他所探求的就是悲傷與理智,這兩者盡管互為毒藥,但卻是語言最有效的燃料,或者如果你們同意的話,它們是永不退色的詩歌墨水。弗羅斯特處處信賴它們,幾乎能使你們產生這樣的感覺,他將筆插進這個墨水瓶,就是希望降低瓶中的內容水平線;你們也能發現他這樣做的實際好處。然而,筆插得越深,存在的黑色要素就會升得越高,人的大腦就像人的手指一樣,也會被這種液體染黑。悲傷越多,理智也就越多。人們可能會支持《家葬》中的某一方,但敘述者的出現卻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因為,當詩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別代表理智與悲傷時,敘述者則代表著他們兩者的結合。換句話說,當男女主人公的真正聯盟瓦解時,故事就將悲傷嫁給了理智,因為敘述線索在這里取代了個性的發展,至少,對于讀者來說是這樣的。也許,對于作者來說一樣。換句話說,這首詩是在扮演命運的角色。 在布羅茨基看來,理想的詩人就應該是“理性的非理性主義者”,理想的詩歌寫作就應該是“理性和直覺之融合”,而理想的詩就是“思想的音樂”。 《悲傷與理智》中的每篇散文都是從不同的側面、以不同的方式關于詩和詩人的觀照,它們彼此呼應、相互抱合,構成了一曲“關于詩歌的思考”這一主題的復雜變奏曲。在閱讀《悲傷與理智》時我們往往會生出這樣一個感覺,即布羅茨基一談起詩歌來便口若懸河,游刃有余,妙語連珠,可每當涉及歷史、哲學等他不那么“專業”的話題時,他似乎就顯得有些故作高深,甚至語焉不詳。這反過來也說明,布羅茨基最擅長的話題,說到底還是詩和詩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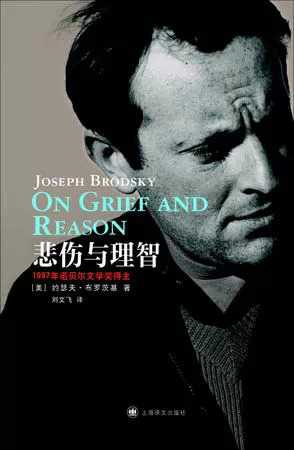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51:02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