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彥文尚在人間
毛彥文簡歷
通過劉紹唐找到毛彥文
她聽罷,搖搖頭:“真是無聊!”
毛彥文為何不愛吳宓
自1998—1999年,三聯書店推出10卷本《吳宓日記》以來,吳宓成了時下學界關注的一位熱點人物。而與吳宓相關的毛彥文女士也引起了更多人士的注意,但對毛彥文女士1949年以后的情況,幾乎很少有人知道,以至于近年來出現了多人多次在文章中把毛彥文女士說成是“90年代初去世”——將活人說死的失實。而事實上,這位跨越三個世紀的老人如今尚在人間。
1898年陰歷十一月一日出生于浙江省江山縣城毛氏大家。辛亥革命后,她先后就讀于江山西河女校、杭州女子師范學校、吳興湖郡女校、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南京金陵女子大學。
1929秋,赴美國密歇根大學留學,主修中等教育行政。1931年夏獲碩士學位后到歐洲游歷,與在歐洲游學的吳宓一同回國。回國后先后執教于復旦大學、暨南大學。
1935年2月9日與前國務總理熊希齡結婚,并主持熊氏創辦的北京香山慈幼院。
1937年12月25日,熊希齡病逝后,他繼承了熊氏的慈幼事業,未曾再婚。
1947年,毛彥文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且一直連任。
1949年4月到臺灣,1950年赴美國。先后就職于舊金山“少年中國報”社、加州大學、華盛頓大學。
1962年回臺灣定居,并執教于實踐家政專科學校,1966年退休。現居于臺北內湖。
在1999年6月以前,我本人也不知道毛彥文女士是否健在。
近期,我的《吳宓傳》、《吳宓與〈學衡〉》兩本書將分別由東方出版社和河南大學出版社推出。這兩天,出版社分別打來電話,告知相關事宜。而我卻急于要將這些消息電告遠在臺北的毛彥文女士。
今天往臺北拔了幾次電話,毛彥文女士家無人應答。我馬上著急起來。心想:這位103歲的老人,是離上帝最近的,不該會有什么事吧?
越想越著急,下午與臺北《傳記文學》社的發行人劉王愛生女士通話。她是前任社長劉紹唐(已于今年2月10日去世)的太太,在臺北我們見過多次面。
劉太太電話中說:毛彥文女士肯定又是住進了醫院。
我說:希望毛彥文女士出院后,能看到我的新書《吳宓傳》。這也是劉社長生前給予過幫助并寄予厚望的一本書。
因為毛彥文女士十分關心我怎么寫吳宓,尤其想知道吳宓1949年以后的生活狀態,更要關注我在傳中如何處理吳宓對她的癡迷單戀。
1999年4月,我的《回眸學衡派》一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吳宓是書中的核心人物。6月中旬,我第二次到臺北作訪問研究。
6月16日下午到臺北,晚上與幾位老朋友在“基督青年會堂”聚餐時,不期而遇《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夫婦。
我是《傳記文學》的作者,且1997年第一次訪臺時,已與劉社長熟識,相聚過多次。他說胡適當年提攜、幫助他辦《傳記文學》,而我這位以《胡適傳》出道的小朋友到臺北,他一定要款待。
送《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回眸學衡派》給劉社長之后,我說:“向劉先生打聽一個老人!”
素有“野史館館主”之稱的劉社長主持《傳記文學》37年,人緣最熟。他問:“打聽誰?”
“毛彥文!”
“熟人。她是我《傳記文學》的作者,就住在臺北。前幾年我還去內湖看過她。”劉社長的話,讓我一陣興奮。因為我早知道毛彥文女士曾為《傳記文學》寫過回憶胡適的文章。
“如今還健在嗎?”我急忙問。
“在!一百多歲了。不過要趕快聯系。這么大年紀,病病怏怏的,怕是見了,讓你掃興。”劉社長翻著我的書,說道。
“我在寫《吳宓傳》,想找到她。這次我來臺北時間較長,請你指教。”
“她是老名人。昔日的國務總理熊希齡太太、國大代表,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她。不過現在的年輕人,就不可能知道毛彥文是何人了!”
劉社長說罷,便提示了幾個了解毛彥文的線索。
18日,我自市內移居內湖,在詩人楊平的母親的幫助下,得知毛彥文在內湖的住址和電話。并于19日清晨與照料毛彥文女士生活的“阿姨”取得了聯系。
21日上午,電話約好后,朋友開車帶我來到毛彥文女士寓所。
這里是一處高級別墅區,住的多是到臺灣的國民黨的老人。
本身沒有子女的毛彥文女士,由一位六十多歲的北方“阿姨”照料,兩人共住一棟兩層樓。
我和朋友在客廳坐下。在“阿姨”的攙扶下,一位滿頭銀絲、面色紅潤的老人從臥室慢慢走出。我和朋友忙迎上去問候。
“阿姨”說:“平時她可以靠扶手椅來回走動。起居飯食都好。原來還能到外邊走動,去年大病過后,身體差了。”
坐定之后,我遞上名片,并自報來意。
“阿姨”要我:“你大聲說話,毛老師耳朵不好使!”
毛彥文女士左手接過名片,右手拿起茶幾上的放大鏡,對我說:“右眼看不見了,這只眼還要用這鏡子。”
她在名片上照了幾下,側頭大聲問我:“這是什么字?”
我知道是名字簡體字中的“衛”又出亂子了。
因為兩次來臺北的經歷中,有過多次這種場面。
和聽力不好的人對話,雙方都要大聲說。毛彥文女士大聲說話,聲音宏亮,使我不敢相信她已是102歲高齡了。
“阿姨”在一旁小聲對我說:“她那只眼白內障動手術,沒動好。現在看報、看信,都是一只眼,用放大鏡。”
我向“阿姨”提出,與毛彥文女士說些過去的事。
“阿姨”忙問:“是說毛老師那個熊先生的事?”
我說:“不是,是其他問題!”
我明白了,毛彥文1949年以后長期在學校執教,所以“阿姨”叫她“毛老師”。
“人年紀大了,100多歲。很遠的事記得清楚。現在的事都記不起了。”說罷,“阿姨”忙其他事去了。
現代史上偏僻的江山縣出了許多名人。“軍統”的戴笠、毛人鳳,炙手可熱,學術界的毛子水,還有這位名噪一時的總理夫人。
與這么大年紀的老名人對話,我還是第一次。也有些緊張,見面前,想了許多,見了面卻不知從何說起。
朋友見我有些緊張,在一旁小聲說:“你慢慢地大聲問她,不可著急。”
我便從沙發上起身,繞過茶幾,坐到她所坐的老人專用安全椅的旁邊,以便說話時她聽得清楚。
“毛老師,我從祖國大陸來看你。”我貼近她耳朵邊,大聲說道。
她有些興奮,也大聲問我:“你是我的什么親戚,還是朋友的孩子?為什么要來看我這個老人?”
“我不是浙江人,家在河南,在河南大學教書。和你一樣,是教師!”
“噢,河南人。教書好。我是從慈幼院教到大學。很多人都叫我老師”。
“我看到祖國大陸出版的熊先生的文集中,收錄有你的照片,是和學生在一起照的,很多人。”我知道祖國大陸湖南師范大學原校長的林增平先生,為整理出版熊希齡文集之事,在80年代初曾與毛彥文女士聯系過。
“你看,那邊有許多祖國大陸寄來的書!我眼看不見了”。她指著另一房間地上堆著的尚未打開包的書說。
不能談熊希齡,若說開去,她準有許多往事要說。我決定把話題引向吳宓。
“我是研究現代文學的,正在研究吳宓,寫《吳宓傳》。”
“研究吳宓,寫吳宓?那和我有什么關系?”
我發現她是在有意問我。
我說:“吳宓為你寫的大量日記和詩詞,最有名的《海倫曲》、《懺情詩三十八首》,如今在祖國大陸都已出版。”
她表示出一些遺憾:“可惜我沒有看到。”
“那些詩文表達的多是對你的愛慕之情!”我進一步發話。
“他是單方面的。是書呆子。”這是吳宓癡迷終生的女性給他的答案和評價。
接著我談了吳宓晚年的不幸遭遇。在說到吳宓在西南師范學院的情況時,她神情嚴肅,并插話:“他還是教授吧?”
我說:“是教授,但和他過去在清華當教授不一樣了。”
“我在美國教書時,那里有吳宓清華的同事,記不起名字了。”
我想她指的可能是吳宓在清華時好友、同事蕭公權先生。因為《吳宓詩集》里有吳、蕭的唱和詩。蕭先生后來在美國還寫過回憶吳宓的文章。
毛彥文女士本身沒有孩子,但熊希齡的后代待她頗好,如同親人。
“阿姨”從里屋走出來為我們加茶水。鄉土的感念,使她插話:
“我家在黃河北,戰亂那會兒,逃難過你們河南開封,50多年了,沒回過老家。”
隨之“阿姨”講到熊希齡的后人對毛老師有很多關愛和照料,尤其是在臺北的親屬,每周都要來看毛老師,或打電話問候。
由此,我想到了在吳宓身上所表現出的世態炎涼。
聽我說到吳宓的后人,毛彥文女士問道:“他孩子都還好?”
這“好”字使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只好說,“都已是老人了。不過她們和你相比,你真是高壽!”
“沒用了,沒用!拖累人。”聽我說她高壽,她的聲音更大。
“吳宓1978年初去世,84歲!是他的堂妹吳須曼,用至愛至親送兄長走完了那段路的。”
毛彥文女士是1962年由美國回臺灣定居的,1976年退休。
我說:“內地這幾年吳宓很熱鬧,尤其是他的日記出版,很多人都知道你是吳宓喜歡的女朋友!”
她聽罷,搖搖頭,回答:“真是無聊!”
“日記中有對你的詳細記錄!”我說。
聽到這里,她表情有些嚴肅:“哎,他寫我,我不知道。”
作為當年的國務總理熊希齡夫人的毛彥文女士,不愿意人們把她與吳宓扯到一起。我送一冊《回眸學衡派》給她,并解釋說:“這是我寫的書,以吳宓為中心,有一章中的幾節專門寫到你”。
她很關心此事,忙用放大鏡看過書名和章目,情緒有些不好,也有點激動,連說兩句:“無聊,無聊!”
談話到此,我發現她頭腦很清楚,也很記事。完全是有意回避談吳宓。我感到再不可以以吳宓為話題了。既然她表示把她與吳宓扯到一起,有些無聊,我覺得自己此時也成了“無聊之人”。
既然一位年過百歲的老人,不愿讓昔日的風花雪月攪扯進今日心頭寧靜的港灣里,那么,我也就知趣退場,好自為之。
我轉過與吳宓有關的話題說:“你可以回祖國大陸看看。”
“走不動了,走不動了。”走動艱難,靠人扶侍的她搖著頭說。
臨別時,毛彥文女士讓照料她生活的“阿姨”,送我和同行的朋友每人一冊《往事》。這是她的自傳體回憶錄,非賣品,印行于1989年。在寫作《回眸學衡派》一書時,我沒能讀到此書。
見她情緒平靜下來,我讓她在書上簽名,她很高興。離開放大鏡,一手持書,一手握筆,她不知道往哪里寫,連打開書幾次都沒寫上字。
我著急了,忙讓“阿姨”為我另備一張紙——“國民代表大會用箋”,將這張紙放在書的封面上,我把書放正,讓她一手拿放大鏡,一手寫字。
她顫抖著手,第一次寫完名字,我發現其中“毛”字少了一橫。
她用放大鏡照照,感覺不對。
我說:“請再簽一次吧!”
她遲疑一下,在旁邊又簽上“毛彥文”三個字。
分別時,我提出要與她合影,她執意不肯,說:“老了,丑樣子。不可以照片示人。”
我能夠理解并體會到像她這樣一位當年的公眾人物,是不愿用今天的一副老態去比照昔日的豐采的。
在友人和“阿姨”的再三勸說,以及我本人的解釋下,她才同意拍照。
從10點20分到11時,共40分鐘的采訪,時間過得很快。想再具體問些有關她與吳宓的往事,又怕她激動,只好起身告辭。
走出毛彥文女士的寓所,我心頭充盈著一種感受,意外見到毛彥文女士,不虛此次臺北行。
回到我下榻的賓館,我夜以繼日讀完了毛彥文女士這本厚厚300頁的《往事》一書。毛彥文女士在本書的序言中說,這本書是在胡適先生的啟發、督促下寫出的。吳宓是反對胡適和白話文新文學的鐵桿人物,但卻瘋狂追求著這么一位新潮女性。毛彥文女士是胡適、沈從文(熊希齡的七弟,為沈從文的姨父)的朋友,也是新文化、新文學的忠實盟友。
我感到奇怪的是,在《往事》一書中,毛彥文女士基本上沒有提及她和吳宓的關系問題,我想她是有意回避的。因為她連1931年與吳宓一起從歐洲回國的這件大事都只字未提。
書中附有大量的照片,同時在附錄中附有一篇《有關吳宓先生的一件往事》的短文。文章簡單地追憶了吳宓一度對她的單戀,和她不愛吳宓的原因。這份材料已被我引進了新出版的《吳宓傳》中。
同時,我更清楚了毛彥文女士為什么不愛吳宓:一個是新潮女性,熱衷于政治、社會公益事業;一個是舊派文人,只會寫舊體詩,寫日記。真可謂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
吳宓為追求毛彥文女士而離婚,并拋下三個女兒。他曾三下江南,一年歐游,結果毛彥文女士于1935年2月9日嫁給了熊希齡。
1937年12月25日,熊希齡病逝于香港。毛彥文女士繼承了熊希齡開創的慈善事業,未曾再婚。她于1947年當選為國民黨的“國大”代表,1949年到臺灣,50年代曾到美國加州大學、華盛頓大學等學府謀職,1962年回臺灣定居,并執教于“私立實踐家政專科學校”,1976年退休。
毛彥文女士如此高壽,且平靜地安度晚年。她跨越三個世紀,本身就是奇跡,何況在吳宓的日記中還有那么多故事。
真想再次訪臺時見到你毛彥文老師!也真切希望你康復出院,看到我的《吳宓傳》。你再說“無聊”也沒關系!只要此書不攪亂你的平靜就好!
我為你祝福!
2000年10月11日
沈衛威 2011-04-11 20:21:24
 |
相關閱讀 |
 |
推薦文章 |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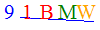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