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景凱旋:契斯,他用寫作抵抗虛無 鳳凰讀書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栗樹街的回憶》/ [南斯拉夫]丹尼洛·契斯/中信出版社/2014-08 景凱旋:抵抗虛無 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人物,出身猶太家庭的他一生經歷了納粹占領、斯大林式統治以及南斯拉夫解體前的民族沖突。由于英年早逝,且喜歡閱讀甚于寫作,他不是一位多產作家,其作品包括兩部長篇小說、三部短篇小說集及三部散文集。他的三部短篇小說集可以看作一個系列,分別寫了兩種不同集權制度下人道的毀滅和原因。其中《鮑里斯·達維多維奇之墓》一書更是被視作繼奧威爾《一九八四》、庫斯勒《正午的黑暗》之后描寫集權清洗的一部經典作品。 這部涉及第三國際恐怖歷史的書出版于一九七六年,立即引起世界文壇的關注,但在契斯家鄉,小說的內容卻招致斯大林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攻擊。這些人避而不談大清洗歷史,而是指控契斯剽竊索爾仁尼琴、喬伊斯、曼德爾斯塔姆、博爾赫斯等人的作品。為了替自己申辯,契斯撰寫了隨筆集《解剖課》,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人文觀念和文學淵源,同時也使讀者得以了解他的生平經歷。 契斯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塞爾維亞小城蘇博蒂察,靠近匈牙利邊境。父親是匈牙利籍猶太人,母親是黑山塞族人,信奉東正教。他從小生活在蘇博蒂察南邊的諾維薩德,那是個橫跨多瑙河的城市,居住著塞爾維亞、匈牙利和德國人。一九三九年,匈牙利頒行反猶法律,父母讓他受了東正教洗禮。一九四一年諾維薩德被匈牙利吞并后,周圍的敵意迫使他父親不斷搬家。童年的契斯始終處在恐懼之中,感到自己無處可去。 一九四二年,諾維薩德發生了屠殺猶太人事件,受害者尸體被扔進冰冷的多瑙河。契斯全家逃到父親的匈牙利家鄉,但在那里也不安全,經常有士兵和警察闖進家里檢查證件,翻箱倒柜。契斯意識到自己仍不屬于這兒,鄉村天主教堂的鐘聲讓他感到神罚的恐懼,他白天在學校學習天主教的教義問答,晚上在家里接受母親的東正教教育。一九四四年,他父親及其親戚被送往奧斯維辛,再也沒有回來。 “二戰”結束后,他搬到母親的家鄉采蒂涅,進入當地一家音樂學校學小提琴。畢業后,他考入貝爾格萊德大學,并獲得首個比較文學文憑。那以后,他一直居住在貝爾格萊德,工作、成家和創作。他的第一部作品發表于一九六二年,最后十年他移居法國,此間只寫了一部短篇小說集《死亡百科全書》,卻接受了大量采訪,寫了不少隨筆,直率地批評國內正在興起的民族主義。他似乎已經預感到,在他的故土,往日的情景將會重現。 童年對契斯的文學成長有著很大影響,他從鄉民那里知道了各種匈牙利神話和格言,從母親那里知道了塞爾維亞的許多抒情詩和史詩,因此很早就意識到所有民族神話的相對性。從這些神話和傳說中,他讀出的是殺戮和死亡。林中仙子與冬天發黑的窗戶、雪地里的槍聲融合在一起,成為纏繞他的噩夢。這種夢境延續到他的文學創作中,他把它歸于母親的遺傳,母親給他講故事時,總是喜歡將事實與傳說混淆起來。 《栗樹街的回憶》描寫的是納粹時期的生活,全書不斷轉換敘事角度,跳動、省略、斷斷續續的片斷,構成每一個章節。兒童山姆的家庭住在栗樹街,有著優美的鄉間景致,他每天的生活雖然艱辛,卻充滿童稚樂趣,放牛、游戲、尿床、初吻、馬戲團、撿蘑菇,各種片斷式的印象構成了一個孩子的現實世界。接下來,周圍發生變化,酒鬼父親從生活中消失了。從幸存的姑媽那里,山姆得知了這個消息,并從父親留下的家族檔案中窺知了部分事實。在孩子的想象中,父親一點也不像一個傳說中的英雄,也沒有給后人留下不朽的遺言,“他們用棍棒和來復槍的槍托毆打他;他呻吟著倒下;女人們為他鼓勁,把他從地上扶起來,然而他——天哪!——哭得像一個嬰兒,他那叛變了的腸胃散發出惡臭”。 家庭的巨大災難敘述得如此平淡,甚至有點戲諷的味道。如果說,小說是作家賦予生活一種形態,那么契斯的世界就是一個超現實的噩夢。這種不連貫的敘事體現了一種后現代主義的寫作方式,簡短的片斷組成繁復的印象,表現出世界的不可解釋性。在創作上,的確可以看出喬伊斯、博爾赫斯、納博科夫、舒爾茨甚至卡夫卡的影響,但對真實資料的使用卻體現了契斯的特色。在此后的《鮑里斯·達維多維奇之墓》中,這種虛實結合的特征得到進一步加強,并形成一種獨特而混雜的風格。 此書由七個故事組成,敘寫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幾個職業革命者的命運。書中的角色都是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愛爾蘭人、匈牙利人、德國人,大多具有猶太血統。這些革命者對這個世界充滿狂熱的恨,在歐洲各地到處發動革命。需要提及的是,他們都是真實的人物,有些在歷史上還赫赫有名。契斯的個人經歷使他十分鐘情于殘酷的史實。經歷了那么多苦難之后,他已不再信任作家的虛構,他找到了自己的敘事方式,那就是在歷史資料的基礎上重建故事。在他看來,“在經歷這個世紀的歷史給予我們的一切之后,顯而易見,幻想以及浪漫主義已經失去其全部意義。現代歷史創造了這樣真實的現實:今日的作家別無選擇,只能賦予它藝術形態,在必需的時候‘創造’它。就是說,用真實的資料作為原始材料,運用新的形式并通過想象來成就它”。 按照契斯自稱的“想象的現實主義”,他把自己變成一個歷史學家,在檔案、回憶錄、傳記和新聞報道中爬梳材料,試圖將散見的事跡連綴起來,呈現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資料里所缺乏的具體情節,以及環境、言行和心理等細節,就用想象來補充。詩人布羅茨基曾評價道:“丹尼洛·契斯明顯詩化的散文帶著對想象和細節的強調,以及反諷的超然,通過提醒讀者注意其本身的智性,將他那恐怖的主題置于最恰當的視角。因此,讀者對被描述的現象的道德評價不再僅僅是心神不安的感傷,而是由他深深刺痛人類的最高智力所產生的評判。這不是思想被感覺,而是感覺被思考。”契斯的作品終究不是歷史著作,而是在歷史的框架結構下,由想象和細節的磚石構成的文學世界。 在此書中,那些第三國際的革命者,無論是知識分子、商人兒子,還是平民子弟,他們的一生都充滿傳奇色彩:暗殺、暴動、參戰、逃亡、流放、被捕、審訊。他們掀起的革命、內戰、集體化在半個世紀里像風暴掃過俄羅斯和歐洲大地,更像是用鞭子抽打著人民的臉龐(書中的一個比喻)。最終,他們無一例外都遭到自己陣營的清洗,在受盡折磨后步向死亡。書中一個人物在童年時寫的詩句得到了應驗:母豬吞吃了自己的豬仔。 書中最長的故事是有關達維多維奇的經歷,他年輕時走過私,當過學徒、碼頭工人和司爐工,組織過罷工、街頭示威、暗殺,然后是苦役和逃亡。十月革命爆發后,他又在俄羅斯與白軍作戰。西方一篇評論這樣描述這位革命家的形象:“他是一個奇特的混合體—沒有道德觀念,憤世嫉俗,對理念、書籍、音樂還有人類有一種天然的狂熱。要我說,他看起來像是教授與強盜的混合體。”革命者的目標就是打碎舊世界,這自然也包括顛覆千百年來的傳統道德。無論對情人還是民眾,達維多維奇和他的同類都是真正的個人主義者,世界圍繞著他們旋轉,而他們則冷冷地看著世界。 所以,達維多維奇被捕后面臨的問題不是革命的正當性,而是“為了那難能可貴、代價高昂的認知,接受這有限的存在之短暫,還是為了這同樣的認知,臣服在虛無的懷抱里”。與庫斯勒《正午的黑暗》相似,那些審訊員都不是教條主義者,也不關心什么歷史目的論之類,他們只是憑著對人類的本能,意識到要讓一個老革命家屈服,就要蹂躪他那多愁善感的自我中心。在地下審訊室里,兩個陌生青年被帶到達維多維奇身邊,由于他拒不認罪,年輕人成了替罪羊,當場遭到槍殺。最后,他不得不屈服了。 在《正午的黑暗》里,被審訊者出于信念和邏輯承認了自己的罪狀,他意識到他與審訊員在維護共同的目標。在《鮑里斯·達維多維奇之墓》里,被審訊者則遭到殘酷的精神折磨,他的認罪是被逼迫的。他并沒有被處死,而是在多年的監禁后越獄,最后面對前來搜索的隊伍,縱身躍進鐵廠的熔爐中。他曾經想要摧毀舊世界,如今卻不想再看到這個新世界。 這是一個關于毀滅與自我毀滅的主題。契斯的文學譜系包括西方許多作家,但在精神內核上,他更接近俄羅斯作家,甚至令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書中人物都是以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要徹底顛覆這個世界,而對于他們建立的新世界,他們仍舊抱著虛無主義的態度。同樣的審訊主題,庫斯勒筆下的人物促使讀者去思考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對革命者動機的隱秘同情顯示出一絲悲劇色彩,而作為年輕一代的契斯對此動機已經十分疏離,他直達事物的核心,以一種后現代主義的超然風格和反英雄形象,讓讀者感到,所有這些殘酷的悲劇是多么的沒有意義。 思考這一歷史的原因似乎不是作家的任務,而是歷史學家的任務。但是,契斯的理性太強,想要在小說中概述和檢討二十世紀歐洲的全部歷史。他的最后一部小說集《死亡百科全書》仍舊保留了一貫風格,故意混淆神話、文獻與想象的界限。全書由九個看似互不關聯的微縮紀事組成,卻有共同的主題可尋:無神論者的死亡。 小說第一個故事是關于西門·馬古的傳說。這個宗教人物見于《新約·使徒行傳》,是一個善行邪術的人。他否認耶穌贖罪的意義,主張靠天啟的知識得到拯救。故事中他一出場,就宣稱耶穌信徒的上帝是個暴君,他許諾了一個不存在的未來,卻剝奪了人類明辨善惡的智慧。西門呼吁民眾不要信神,而是信從他本人。為了爭取民眾的信仰,西門甚至顯現奇跡,緩緩飛上了天。人們紛紛跪下膜拜,因為很明顯,如果這一奇跡是真實的,那么基督教的信條便是值得懷疑的了。 早期的基督教作家都認為,西門是異端諾斯底教的開端。從十九世紀迄今,一直都有諾斯底教派的古文獻流傳。按照這些文獻記載,人的墮落不是由于原罪,而是由于無知。這種唯智論否定基督教的意義世界,導致了價值虛無。現代學者約納斯就曾把諾斯底看作存在主義的古代對應者,認為可以借助它洞察現代虛無主義的意義。契斯將這個故事放在開頭,似乎也是在暗示諾斯底思想與現代人精神的聯系。 面對一個沒有上帝的物理世界,現代人感到基督教建構的倫理秩序消失了。存在只是一種物質的偶然,沒有任何意義。人來到這個世上,失去了不朽的撫慰,只有絕對的孤獨和虛無。小說中無論是妓女、貴族革命者,還是哲學家和詩人,對他人都充滿怨恨或冷漠。面對死亡的臨近,他們發現自己一生孤苦伶仃,對死亡充滿恐懼。旁人對他們的悼詞將會充滿頌揚,但他們自己知道,“只有死亡是確實的”。 書中還寫到諾斯底文獻中出現的其他主題。比如,書中人物思考的“無性即是與道德無關”,這正是諾斯底的道德無涉主義,禁欲可以輕易變成縱欲;書中人物思考的“面對他人的空虛是危險的,即使只是注視著這空虛,這就像是在深井里注視著自己的倒影:因為那也是空虛。空虛的空虛”,這正是諾斯底所主張的現象就是實體的結果,人被擲入一個無神的自然之中,他為自己設計的意義實際上沒有任何客觀意義。 以虛無始,以毀滅終,這就是二十世紀歐洲社會道德崩潰的過程。契斯特地寫到一份題名《謀反》的反基督教文獻。這份不知所出的文獻流傳于世紀之交的歐洲,甚至在沙皇和蘇維埃內戰的白軍中流傳。根據契斯所引用的研究,它的政治現實主義還影響了希特勒、斯大林和福特公司的老板。這本類似馬基雅維里理論的《謀反》成為現代《圣經》,播下猜疑、仇恨和死亡的種子。以下是《謀反》的兩段摘錄: 當我們征服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要把“自由”這個詞從人類的語匯中抹去,我們要將此視為己任。因為自由是生命精神的化身,它的力量能使人群變成嗜血的野獸,不過,當然了,就像所有的野獸一樣,一旦讓他們喂飽了血,他們就睡著了,所以很容易管教。 政治與道德毫無共同之處。一位有道德地治理國家的統治者并不是政治家,因此無權居于高位……結局自將證明方法的正當性。所以,讓我們將何為善良與道德擺在一邊,專注在什么是必要的、有用的上面吧。 在接受采訪時,契斯曾稱他在此書中的思想是諾斯底式的,但這也可能是契斯的障眼法,目的是讓讀者把他視作一個冷漠的后現代主義者。就契斯全部作品的主題而言,他把兩個世紀來的政治迫害歸于人類的道德淪喪,而在這種毫無意義的殘酷背后,則是對世界的一種虛無主義看法。因此,此書中表現的諾斯底思想與其說是在肯定道德冷漠,毋寧說是出于強烈的倫理情感,試圖探尋現代虛無主義的根源。正如詩人布羅茨基所指出,契斯的作品“在倫理失敗的地方達到了美學的理解”。 契斯想要指明的是,兩個世紀以來的仇恨、迫害、屠殺無不源于虛無主義的世界觀。這股虛無的力量曾一度征服了全世界的人心,看上去似乎不可戰勝,能夠戰勝它的唯有它自身的限制。正如書中的西門最終從云端跌下塵埃,證明了他不過是一個假先知。這似乎是一個隱喻,建立在虛無主義基礎上的現代極權由于其道德虛無,終將會自我毀滅。 一九八九年十月,契斯在法國因病去世。在他的名聲遭到毀謗時,有許多人站出來支持了他,這其中就有俄裔詩人布羅茨基和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前者為《鮑里斯·達維多維奇之墓》的英文版寫了序言,稱揚他的作品重新定義了悲劇。后者將契斯的《解剖課》和其他文章編輯成書,在序言中感嘆:“他的辭世中斷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全世界作家中最重要的文學旅程。” 契斯生前曾目睹集權制度正在東歐崩潰,民族主義再度成為主流。他對此曾經寫道:“民族主義是最大的偏執狂,個人和集體的偏執狂。民族主義者沒有任何問題;他知道—或認為他知道—他自己的基本價值,他自己的人民的價值,他所屬的民族的倫理和政治價值。他沒有任何其他興趣。沒有其他東西能引起他的興趣。他人就是地獄(其他民族,其他種族),不值得了解和研究。所有民族主義者在其他民族那里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形象:一個民族主義者的形象。民族主義的興盛基于相對主義:它沒有普世價值,美學的或倫理的價值。” 契斯將這個普世價值淪喪的虛無時代看作一個神話世界,現代人仿佛處在世界的原初,沒有統一的倫理秩序,一切都是未知、混亂和盲目的。受到某種種族或歷史宿命論的驅使,人類瘋狂地互相殺戮。唯一不同的是,古典神話中的毀滅還有著悲劇的慰藉,現代神話中的毀滅只剩下虛無的灰燼。正如克羅地亞哲學家勒達·米舍維奇所稱,鼓動南斯拉夫宗教分裂的“主要都是無神論者”。契斯沒有親眼看到南斯拉夫的分崩離析,沒有看到集中營和種族滅絕的重現。如果契斯依然健在,他會將此看作該隱殺亞伯的虛無主義演繹,另一場現代諸神的戰爭。 蘇珊·桑塔格曾說,契斯的作品“維護了文學的榮譽”,那是因為他用文學回應了這個時代,在展示集權災難的同時,表現出一個作家對人性的關懷。他用優美的文字描繪出人的一生的諸多細節,讓我們在驚懼和思考之余,仍能享受到美學上的愉悅。比如,書中一個人物在查閱《死亡百科全書》時看到了父親的一生,這是一本記載一七八九年以來全世界所有普通人事跡的秘密文獻:“在那些孩子中間,我清楚地看到了他,我的父親,雖然當時他還不是我的父親,但是他是將成為我父親的那個人,曾是我父親的那個人。然后,鄉間忽然間變綠了,樹梢的花蕾綻放了,粉紅的,白色的,山楂花就在我眼前綻開。太陽緩緩上升,照耀著克拉列維察,鎮上教堂的鐘敲響了,牛在牛舍里哞哞地叫,朝陽緋紅的反光映在農舍的窗戶上,融化了屋檐上的冰柱。” 這就是文學,最終還是想象拯救了事實,抵抗了物理世界的時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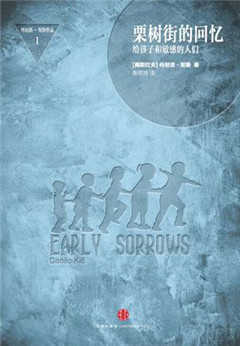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1:31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