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動物園(短篇)∣《文學青年》甫躍輝專號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該小說入選2012年度洪治綱花城出版社《中國短篇年選》;2013年8月,入選吳義勤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必讀》短篇卷第一輯;首屆人民文學之星獎;第十屆十月文學獎新人獎 虞麗三個星期沒來,顧零洲又過上了單身生活。這周末,報復似的睡到了下午四點,餓得受不了了,才起來煮了方便面。吃完后,開始看美國國家地理的紀錄片。這曾經是他無上的享受,和虞麗在一起后,竟然沒再有過。去他媽的吧,他這么想著,接連看了三集。最后看的一集是《象族》,當大象的身影從攝影機前慢慢遠去,解說員說:“大象的生活充滿了莊嚴、溫柔的舉止和無盡的時光。”顧零洲無限感慨地回味著這句話,抬起頭來,窗外已黃昏。暮色溫柔地籠罩了動物園,游人正在散去,一切漸趨靜謐。隔著窗,看得最清楚的正是大象的領地。他看得清楚,有十二頭亞洲象,厚重的身軀覆滿紅色的灰塵,矗立在寸草不生的泥地上,像一堵堵沉默的紅磚墻。 他驀然想到,那天,他們竟沒去看大象。他原本想,一定要帶她去看看大象的,因為站在大象的領地邊,正好可以看到他們小小的窗戶。 他抓過手機,打了一句話:“這周末可以過來么?”想了想,把“可以”兩字刪掉,發了出去。他忽然覺得,不會有回音的,她可能從此消失了。這段時間,他一直恍惚覺得,她似乎從未來過。--不過虞麗很快回了消息:“好呀,前段時間太忙了。”他仔細咀嚼著這句話,知道她已經不生氣了。他回復道:“上次的事很抱歉,以后--”他不知道是不是該說,他以后想要帶她去看看大象。他遲疑著,最終刪掉“以后”,把短信發了出去。好一會兒,她只是簡單回道:“沒事了,下周見。” 顧零洲到地鐵站接她,出乎他的意料,她似乎徹底忘了上次的不快,臉上盡是輕俏的笑,“老公”,她低聲喊他,旁若無人地在他嘴邊啄了一下。虞麗一句沒提上次的事兒,顧零洲也不再提。回到屋里,虞麗放下挎包,徑直走到窗邊,拉開窗簾,關上窗戶,重又拉好窗簾。回過頭來,顧零洲正盯著她。 “看我什么?”她莞爾道。 “沒什么。”顧零洲遲了一會兒,嘴角也往上翹了翹。 “老公不想我嗎?”虞麗瞟了一眼床,又瞟了一眼他,眼神中滿是溫軟的俏皮。 “想呀,怎么能不想?”他有點干巴巴地說。 抱在一起時,仍舊有一點勉強。顧零洲持續了很久,腦海里不斷閃現出那句話:“大象的生活充滿了莊嚴、溫柔的舉止和無盡的時光。”這話讓他莫名地焦躁。后來,虞麗柔聲道:“停下來,好嗎?”他才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氣。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不知道怎么,一點感覺沒有。”虞麗輕聲說。 顧零洲把她抱緊一些,心里莫名地充滿了歉疚。 大體上說,他們恢復了過去的生活。顧零洲發現,唯一不同的是:虞麗以近乎執拗的態度堅持關窗。以前,她也會要求關窗,但總是撒著嬌征求他的意見:“老公,我們把窗子關上一會兒好不好?”現在,不了。只要一看到窗戶開著,她立即會關上。哪怕窗簾拉著,她一聞到空氣中那股臭味兒,也會很警惕地拉開窗簾查看窗戶關了沒有。其實,顧零洲也不喜歡那味兒。但他喜歡開窗,屋子本來就小,老關著門窗就會顯得愈發小。在屋里待久了,他會有種窒息的感覺,就如一條被悶在密閉水箱里的魚。他將什么也做不了,就像那頭走來走去的獅子,只能不停地走來走去。 …… 他們默默地恪守著一條原則:不在對方眼皮底下去關窗或開窗。雙方的戰爭成為名副其實的“暗戰”。表面上,始終保持著應有的禮節;內底里,其實寸土不讓、硝煙彌漫。戰爭很快由白天蔓延至夜晚。兩人躺在床上,總是暗暗較勁兒,看誰先睡著,先睡著就意味著放棄了對窗子的控制權。為了迷惑敵人,兩人在偽裝上都下了大功夫。顧零洲的偽裝方式是打鼾,她知道他很少打鼾,為了不至于引起她的懷疑,他裝作鼻塞。響了兩三聲后,她小聲嘟囔了句什么。他試著調大一點聲音。他的嘴巴和她的耳朵挨得很近,他相信,在闃寂的夜里,這可以說是聲若驚雷了。她只砸吧了一下嘴。睡得真夠香的,他無聲地笑了一下,慢慢從她脖子底下抽出手臂,起身推開了窗戶。為了保證不發出一點聲音,他推得極其小心,推開一點,又回頭覷她一眼。月光下,她的臉安靜而柔和。花了三四分鐘,他才推開了窗戶。夜晚的空氣清冷、潮濕,什么味兒也聞不到。他眺望著月光下的動物園,大象影影綽綽的,在人們安睡的夜里,它們仍清醒著。這樣靜謐的時刻,他才真正體會到那句話的含義:大象的生活充滿了莊嚴、溫柔的舉止和無盡的時光。 一早醒來,顧零洲發現窗戶關得嚴絲合縫。 他有點恍惚,難道昨晚自己并沒開窗?不對啊,他分明記得自己的一舉一動。想來想去,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虞麗也像自己一樣裝睡,或者半夜醒來過。他偷偷觀察她,她沒露出一絲一毫的破綻,完全是一副無辜的樣子。還裝得挺像的,顧零洲在心里冷笑了一聲。他并未由此退縮。除了躺下后努力爭取最后睡著,他還想出了一個絕招,就是睡前多喝水。這樣,便能保證他半夜醒來上廁所,也就能夠保證半夜在檢視一遍窗子。漸漸的,他又更進一步,摸索出喝多少水便能在天亮前醒來,這樣,可以在白天到來前最后檢查一遍窗子。然而,一切都是徒勞。不管他怎么努力,他早上一覺醒來,窗戶總是關著的。他一次次懷疑,睡前開窗加上夜里復查,難道都是夢里發生的事兒?如果不是,那虞麗是怎么做到的?太不可思議了。簡直可怕!她對他的一舉一動明察秋毫,他卻對她的所作所為懵懂無知。他看她的眼神,越來越充滿了困惑。他總是怔怔地盯著她看,她有太多他所不能了解的了。她是如此熟悉,又是如此陌生。 就連做愛時,他對她的困惑也未能消解。他盯著她緊闔的眼睛,心想,她多像一個無法破解的謎呵。或許是太三心二意,整個過程變得冗長、拖沓。汗水密密地布滿了他的額頭,屋里熱得像個蒸籠。鬼使神差的,他微微側了側身,伸手探過窗簾將窗子推開了一條縫。猛然間,他感到身子一顛,摔在了床上。虞麗背對窗簾,面無表情地瞪著他。 “顧零洲,你究竟想怎樣?” “什么怎么樣?我不想怎樣啊。”他有點懵。 “沒神經病吧你?” 顧零洲瞪著她,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樣的質疑。 “你對我究竟有什么不滿?就因為那天在動物園里我生氣了嗎?你不知道那股尿騷味兒讓我多難受!可我一直堅持著,陪著你逛了大半天!我一兩周才過來一次,你就不能遷就我一下,把窗戶關上?你喜歡聞屎尿味,就不能等我離開后聞嗎?就算我一周過來一次,那七天里你還可以有五天盡情地聞啊,你怎么就連兩天都不能等!你怎么就這么自私!”虞麗拉過被子堆在身上,深深喘了一口氣,語氣緩和了一下:“你想想,和你在一起這么久,我對你要求過什么?別說房子,就連衣服也沒讓你給我買過一件!這些我都不在乎,只要我們志趣相投就好。可你呢?我不提要求,你就從沒想過要給我什么嗎?連關窗這么一件小事都不愿滿足我?” 虞麗抽噎著,淚水順著臉頰往下滾落。 顧零洲慢慢地紅了臉,汗水一層一層地從不知什么地方冒出來。 “不是這樣的”,他支吾道,“我只是想讓你知道,其實那氣味沒什么……夜里更沒什么,什么氣味也沒有。” 虞麗不解地瞅著他,張了好幾次口,才說: “不是我說話難聽,你真沒毛病吧?你說過的,我是你遇到過的最知心的人,我也曾經認為,你也是我遇到過的最知心的人,我從來沒跟誰談論工作那么投機,可是,現在你越來越讓我搞不懂了。你難道還想成為動物學家?想要我跟著也成為動物學家?你喜歡的,不能強制我也喜歡啊。別胡亂找理由了,其實,你不斷開窗,只是想讓我不舒服,想讓我不高興。很簡單,你想折磨我!你知不知道,跟你在一起,我有多少夜沒睡覺了?!我以為,只要堅持關窗,總有一天你會醒悟,會心疼我遷就我,可我想錯了!” 虞麗濕漉漉的眼睛里卻閃爍著仇恨的光芒,有一把火隨時要燒到他身上似的。不知道她那瘦瘦的身體里,怎么會潛藏著如此巨大的力量。 “不是……不是這樣。”顧零洲磕磕巴巴的。被虞麗這么一說,他也開始懷疑自己了--我為什么就那么想開窗? “不管是不是吧,你對我來說就像一個謎。我喜歡你,可就是猜不透你。現在,我真的累了,不想猜了。”虞麗眼里仇恨的火焰被不斷淌下的淚水熄滅了。 沒有虞麗的日子,顧零洲仍舊保持著幾周來養成的習慣,臨睡時喝下足夠天亮前一刻醒來的水,躺下后假寐一會兒,然后檢視一遍窗子,天亮前起來上廁所時再檢視一遍。不過檢視的內容有所不同,現在,他是為了確認窗子關好沒有。自從虞麗離開后,他一直關著窗子。他想試驗一下,自己能否為了虞麗做一次徹底的改變。 顧零洲深感生活陷入了一團迷霧中,他既想看清去路,也在竭力回想來路。高考讓他誤打誤撞地來到這座城市,畢業后到了現在的出版社,同時到了現在住的地方。快畢業那段時光,他總是惶惶不可終日,担憂自己無法適應學校外的世界--工作和生活,都讓他緊張。然而,時間一天天催逼著他去面對。他在同學的介紹下找到了現在的住所,房東向他推介房子,說他可以天天免費看動物園了。他至今記得,房東的這句話給了他很大的安慰。那時候,他想起了年少時對動物園的印象,想起了自己曾有過的“動物學家”的綽號,以及要做一個“動物學家”的夢想。 回望近三十年的生命,顧零洲驚訝地發現,自己幾乎沒什么夢想可言。從小到大,他哪方面都不算突出,不會給別人留下什么特別印象。換種安慰的說法,也可以說他哪方面都還可以。進出版社做美編,并非他的夢想,只是他的第一份工作罷了。他適應了,并且喜歡上了--偶爾,他會誤以為自己從來就喜歡這個。他幾乎沒想過換工作。那太危險了,他必定又會如快畢業前夕那樣惶惶不可終日。算起來,“動物學家”算是他有過的唯一的夢想了。那么,他現在算是緊挨著夢想生活吧。 是這樣嗎?這就是我的夢想?好像,又不是。他站在緊閉的窗前,下意識地辨識著夜色中大象們巨大的身軀。他很少計劃什么,也很少堅持什么,同樣,很少思考什么。他的生活就是順著一條不需要掙扎的軌跡往前滑動。高考、工作、租房,莫不如是。就連和虞麗在一起,他也有這樣的感覺。他想,若非通過網絡,他可能不會有勇氣對她說那樣的話。他本科時有過一個女友,也是在網上認識的。他們沒有任何可以交流的話題,即便如此,他也沒想過要離開她,直到她大學畢業后離開這座城市。他沒和她一起離開,因為他實在沒有勇氣去面對一個全新的城市。 現在,他想有所改變了。他不止一次回想起和虞麗生活的情形。他會想象著她的形象自慰,然后心里變得愈加空落落的;會忽然想起一些細節,譬如她的水草一樣涼絲絲的頭發滑過他胸口的感覺。他回過神來,看到窗外已是暮色沉沉,動物園里的樹梢浮著一縷嘆息似的橘黃色夕光。他感到茫然的生活被賦予了某種意義。他給她發短信解釋說,他之所以那樣做,真的只是想讓她對動物園破除偏見。他并不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強加給她--再說,動物園也并非他寄寓理想的地方--只是,很想帶她去看看動物園里的大象,因為在大象邊,可以看到他們的房子。他知道這是個聽起來很難成立的理由,但他不知道除此還能怎么解釋。她沒表示相信,也沒表示不相信。他以為她理解了他。他一次次問她什么時候能過來,她總說最近太忙,過一陣子再說。她曾說過,她住的是老師們的集體宿舍,不方便讓他過去。現在,他真想去找她,看看她在自己之外有著怎樣的生活。一個多月后,他再發短信讓她過來,許久,她回短信說,我們分手吧。 …… 又過了一個星期,虞麗來了。是個晴朗的下午。顧零洲一直設想,兩人再見面會是怎樣的情形。其實沒什么特別的。虞麗一進門就脫了外套,往手上呵著氣說:“屋外還挺冷的。”已是初春時節,天氣似乎并沒轉暖的跡象。顧零洲笑了笑,“那就別忙著脫衣服啊。”虞麗還是脫下了大紅色的長風衣,隨手擱在床上。她穿一件嫩黃色毛衣,令顧零洲心頭一陣暖熱。 “你這屋里味道這么重!”虞麗瞥一眼顧零洲,擰著眉頭。 “一個多月沒開窗了……可能有點兒”顧零洲紅了臉,轉身想要推開窗,又停住了。他覺得很尷尬,不知道怎樣做才是合適的。 虞麗似乎也有些尷尬。很明顯,她沒想到會這樣。她慢慢地舒展開了眉頭,低了聲說:“那我收拾一下吧,你做你的事,別管我。” 顧零洲目光溫軟的蛛絲一般粘在她身上。看著她收起她留下的拖鞋、內衣、鏡子、毛絨熊、化妝品等小東西,同時,像往日一樣收拾床鋪、擦凈桌椅,還拖了地板。為了不妨礙她,他不時挪一下位置,像一件多余的破舊家具,不知道該往哪兒擺放。她注意到他一直盯著自己,抬起頭瞟他一眼,一瞬間,眼睛里閃過一點什么東西,又低下頭去。“你做你的事呀,別管我。--我沒打攪到你吧?”她異常客氣。 她不停地在屋里走動,白皙的臉變得紅撲撲的,不時抬起手背擦拭額頭。后來,她干脆卷起了毛衣袖子。不過,不管如何仔細,屋子畢竟很小,不到一小時,實在沒什么可收拾的了。只是,那濃重的氣味還在。 “要不,開一下窗吧?”她遲疑地看著他。 “你……能習慣嗎?”他探尋地問道。 “還好吧,”她莞爾道,“透透氣總比悶著好。” 他也笑了一下。一個多月沒開了,窗子有點兒不大靈活了,他用上兩只手才推開。霎那撲來的空氣竟讓他有點兒難以適應。這就是動物園的氣味?他有些疑惑地想。 他們并排站在窗前。他看到她大大呼吸了幾口氣,帶著動物園氣味的空氣。 “那我走了。”她輕聲說。 他感到心頭突地跳了一下。他攥緊拳頭,又松開,再攥緊。她仍舊和他并排站著,并沒有走。他鼓起了很大勇氣,把手抬起,搭上她的肩頭。他如同機器,扭過她的身子,把手放在她的臉頰上,她的臉頰有著薄薄的初生雞蛋似的溫熱。她怔怔地盯著他。他也怔怔地盯著她。她的眼眸深處閃爍著一點亮晶晶的東西,是那么……熟悉。這時,她輕柔而又堅決地推開了他。“別這樣,”她輕聲說。又扭動了一下肩膀,好擺脫掉他的手。一瞬間,他回過神來,不禁又想,他們簡直是陌生人。這感覺像一道魔咒,再次牢牢地箍住了他。 “沒什么事的話,我走了。”她開始穿風衣。 “我帶你去動物園里看看大象吧?”他忽然說,連他自己也吃了一驚,“在大象身邊,可以看到我們的屋子。我們晚上去,就不會有氣味了。” 她瞅著他,驚訝得張大了嘴。 “你讓我說什么好……對你,我當真是無語了。”她果斷地挎了包,“你那么想去,跟你以后的女朋友去吧。” 虞麗堅持不讓他送,獨自拎著包走了。他趴在另一邊窗口,望著她走出自己這幢樓,一徑走出小區,始終沒有回頭。不到五分鐘,她的大紅的長風衣如一束火焰熄滅在路的拐角處。他呆呆地趴在窗口,凝望著拐角那兒。那一束火焰似乎還燃燒在他的眼睛深處。即便閉上眼,仍能感覺到它在眼簾上熊熊燃燒。再睜開眼睛,他才確認,她消失了。他突然拔腿往下跑,一心想要追上她。他想,他應該和往日那樣送她到地鐵站的。他追出了小區,追到了動物園門口,放眼望去,地鐵站前這一段路上已經沒她的蹤影了。初春的明晃晃的,使得柏油馬路蜿蜒成一條波動的河流。他沒再追下去,氣喘吁吁地坐在動物園前的馬路牙子上,不知道接下去該做什么。 不知坐了多久,暮色在馬路上涂下他孤零零的影子。馬路上盡是下班回家的人。他木然地站起,兩眼茫然,不知是不是也該回家去。一轉頭看到了動物園的大門,不斷有人往出走,快要閉園了,再有幾分鐘就不讓進了。他毫不猶豫地朝大門走去。 他拐過曲折的路徑,徑直往大象區走。對這家動物園,他實在太熟悉了。可不知怎么,走了半天他才發現迷路了。他又回到了猴子們的假山旁。猴子們嬉皮笑臉地笑話他。他不理會它們,疑惑地望著來路,皺著眉,慢慢讓自己平靜下來。好一陣子,他才發現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錯。他小心翼翼地繼續朝大象區走去。暮色越來越重,樹影越來越重。他仿佛走在無盡的時光中。看到大象的那一瞬間,他終于難以自已,感到淚水一再涌滿眼眶。透過淚水,他看到了夕陽下正咀嚼著干稻草的大象們。此時,他莫名地覺得,它們不再是莊嚴和溫柔的,它們赭紅色的龐大身軀里,似乎隱藏著同樣龐大的痛苦。 避過清園保安的視線,比想象中得要簡單;在夜色的迷障和十來棟樓的迷宮里辨識自己的窗口,卻比想象中難多了。他背靠大象們的圍欄坐著,盯著一處黑洞洞的窗口,卻總不能完全確定那就是自己的窗口。大象們在不遠的黑暗中,它們在睡覺么?大象的睡眠時間很短,只有短短幾分鐘。如果它們做夢的話,可能都來不及回到家鄉吧?這么想著,他想回去了。這兒并沒想象中的特別,再說,初春時節的夜還是挺冷的。他出門時只沒穿外套,瑟縮著,又望了一眼黑暗中大象們小山丘似的身軀,覺得自己就如一只受傷的動物,要回到自己的窩里去了。一路上,他覺得自己心里是那么柔軟,那么孤獨,又那么平靜。走到大門邊,他才發現棘手的問題:動物園的大門黑沉沉地關著。 2010年12月6日6:30:41師大一村 本作品由甫躍輝授權《文學青年》發表,轉來請注明出處動物園(節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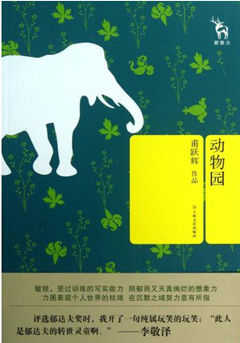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3:02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