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跟張子謙先生學琴 成公亮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張子謙先生上世紀40年代在琴磚上撫琴的照片,下有沈草農先生題詞 1958年秋天開學不久,我們忽然被告知,教務處安排了新的古琴老師,是張子謙先生,都去跟他學。這一年大學部民樂系考進來兩個古琴學生,林友仁和劉赤城,劉景韶先生也許是被安排去教他們了吧。張先生本人的工作單位是上海民族樂團,從校外請來兼任古琴教學,與劉先生是學校里有編制的正式教師不同。 前面說過,這一階段金村田先生在學校教學里推行“民族化”,直接結果就是,不少學生響應號召,從西方音樂轉到民族音樂上來。我的同班同學里,鋼琴專業的項斯華、范上娥、許潔如、朱元貞、忻愛蓮、高星貞,長笛專業的張念冰,后來還有第二批張燕燕等,紛紛改學民樂:古箏、琵琶、揚琴、三弦……這批同學高中畢業之后進入上音大學本科,再過一二十年,其中不少人成為中國民族音樂的中堅力量,甚至成為大師級的演奏家。其中,高星貞學的是琵琶,到了最后一年,又改學古琴。 我最近看張先生的《操縵瑣記》,在1958 年10月8日這一天,記載了他第一次給我們上課的感受:“晨開始往音樂院附中兼課教琴,學生成功(公)亮、龔榮生、李禹賢已有一二年程度,指法均相當好。音院目的在吸收各家指法,培養出全面人才,但運指方面欲徹底改變,頗有困難,如不改變,則一家風格決難彈出,縱下一番功夫,恐不易達到十分完美也。”10月8日這個時間,我已經記不得了。一般開學在9月,可能當時學校剛剛從漕河涇搬到市區,雜務比較多,或者學校里安排課程、聯系老師、辦理手續什么的,有一些耽誤。 我跟張先生學了兩年。高三那一年,跟他學了廣陵派的《平沙落雁》,然后是《龍翔操》和《梅花三弄》,也就是他最負盛名的“老三曲”,都出自清代的《蕉庵琴譜》。張先生的教學方法跟劉先生一樣,對彈。不過他這個人和劉先生最大的不同,是愛說話,話多得不得了。過去沉悶的感覺一下子全沒了,每次上課都是輕松的,我就特別喜歡上他的課。 學廣陵《平沙》時,因為剛學過梅庵《平沙》,心里就有個比較。梅庵《平沙》安靜之外還很生動,我很喜歡。廣陵《平沙》是另外一個味道,比梅庵的《平沙》安詳沉著。不僅彈法風格上不一樣,意境不盡相同,琴曲曲調也有許多不一樣的地方。我學了廣陵的《平沙》之后,梅庵的《平沙》就不彈了,兩個曲子容易竄。張先生教一首曲子之前,給我們每人一份譜子,這份譜子是簡譜和減字譜對照的,用普通的橫線條信紙墊上印藍紙復寫,上面標著“張劍記譜”。張劍是他們團里一個彈柳琴的演奏員,跟張先生接觸比較多,經常給他記譜。 到了《龍翔操》和《梅花三弄》這兩個曲子,張先生的風格特點就顯露無遺了。他的風格特點,我現在的認識是:中國音樂的自由和不均衡的節拍節奏,在古琴上體現得最為典型最為明顯。而在古琴的幾個流派里和個人風格上,張先生是與眾不同的一位,他把這種審美特點發揮到極致。特別是《龍翔操》,在這里,表達音樂最重要的手段不是曲調旋律,而是自由跌宕的節拍節奏變化,是琴曲樂句頻繁的速度變化,他的音樂充滿“動感”之美。這種表現音樂的手法很少見,這是我最近幾年的分析和認識,而在五十年以前,體會是不深的。跟他學《平沙》、《龍翔》和《梅花》,也就是模仿而已,粗聽起來比較像,甚至可能一模一樣,但實際上他那種自由自在的靈魂上的東西并沒有能夠真正掌握、領會。所以,當時我對《龍翔》和《梅花》興趣不是很濃,興趣不濃肯定也彈不好。我所有的唱片中,這兩個曲子從來沒有錄過音,原因就是這兩首曲子我彈得不好,根本沒有學到張先生琴曲的精神。 張子謙1957年手抄《龍翔操》簡譜減字譜對照譜(第一頁) 那時候我們都知道一個關于張先生的故事:大概二十年前,張先生和徐立孫先生交流琴藝很多,徐先生曾經毫不客氣地當面說他“下指不實,調息不勻”。張先生呢,不但不生氣,還拿這話寫成一副對聯“廿載功夫,下指居然還不實;十分火候,調息如何尚未勻”,掛在墻上,作為自勉。徐先生坦誠,張先生謙虛,這個故事流傳非常廣,成了佳話。不過,大家好像都滿足于“佳話”,沒人從觀點本身去探究一下。“下指”說的是指力,徐先生彈琴,下手很重,這是他個人的審美和習慣,以他的指力去衡量張先生,自然“下指不實”了。“調息”體現在節奏節拍上,張先生吟詠式的節拍節奏自由跌宕、隨心所欲,有一種充滿動感的、自由自在的“律動之美”。他的《龍翔操》“通體散彈”,《梅花三弄》搖曳、動蕩的泛音節奏,讓人無法給它打拍子,在當時也沒人會用這樣“不準”的節奏來彈琴。而徐先生彈奏的琴曲節拍節奏相對比較規整,他整理的《梅庵琴譜》都點了節拍,這也正是梅庵的彈法。這樣,徐先生自然要說張先生“調息不勻”了。張先生是個特別大度的人,朋友提了意見,他覺得應該虛心接受。作為一個演奏家,他并未從理論上仔細思考分析,而在實際演奏中也并沒有改變原來的彈法。如果他把自己的“律動之美”都改變了,哪還有“張龍翔”呢? 附中的學習并不緊張,張先生又是那么有趣和可以親近的人,我們平時就常去他在常熟路的家里玩,我去得尤其多。徐匯區的東平路附中、汾陽路大學部,和常熟路正好是一個三角。常熟路上有個上海實驗歌劇院,實驗歌劇院的大門前右方有一棟樓,樓前圍墻一側的木門平時是開著的,可以隨便進入。張先生就住在三樓。樓的木門邊上,有根鉛絲一直從這里通到三樓公用樓道的窗戶,那頭裝了一個彈簧,彈簧一端安了一個鈴鐺。我在下面一拉這個鉛絲,上面鈴鐺就響了。過一會,如果窗戶上露出張先生的半身,喊著“來啊來啊”,我就上去。張先生的客人多,拉了這根鉛絲和鈴鐺,一旦他不在家,客人不會冤枉跑一次三樓。 張先生一個人住——我后來才知道當時他太太去世不久。他家里比較寬敞,房間里掛著一張他在琴磚上面彈琴的照片,大概張子謙先生家中懸掛的40年代撫琴照片,下有沈草農先生的題詞,大概五十來歲的樣子,照片下面有很多沈草農先生寫的字。后來我發現,他家無論搬到哪兒,這張照片都掛在客廳墻上。 坐定后,先倒茶,然后就開始聊天。聊天是我和張先生之間的重要內容,幾乎比彈琴還重要。聊的話題很雜,什么都談,沒有偏重,關于古琴的只占了很小的比重。不過,現在看來,也許是關于古琴的內容最有價值吧。 張先生一般都會講講最近的事情,也常講民族樂團和今虞琴社的活動,或者誰來學琴……民族樂團的演出有一些,我去聽過一次,那次有張先生的古琴獨奏節目。古琴音量小,擴音往往也搞得不好,演出效果很一般,和其他民樂沒太顯著的差異,甚至沒有其他節目受歡迎。難得的是,演出里還有沈德皓唱的琴歌。這些古琴音樂可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歡迎和重視的節目,在樂團里面維持下來,真不容易。今虞琴社的活動,當時我沒參加過,因為張先生的關系接觸了幾位前輩琴人,但也不算熟悉。 社會上偶爾有人很熱情地來學琴。哎呀,那時候有人學古琴,彈琴人開心得不得了——總算是有人喜歡我們的東西啊,教起來特別盡心。可來人稍微學學,又覺得沒有原來想象的那么好學好聽,沒多久興趣淡了,就不來了。張先生也會邊嘆氣邊跟我講:“唉,怎么這樣!開始有興趣的,現在不來啦!”他在《操縵瑣記》里就無奈地感嘆這樣的學琴者:“盲目而來,盲目而去。” 張先生經常談到的名字,是沈仲章、吳振平、姚丙炎這幾位和他來往密切的琴友,還有就是査阜西、吳景略、彭祉卿三位老友。那時候彭祉卿去世已經十多年了,査阜西、吳景略都已經去了北京,但他時常掛在嘴邊。我那時還沒見過査阜西先生,吳景略先生偶爾回上海,可能見過一兩次。衛仲樂先生、劉景韶先生,他和他們交往不多,也很少談起。 張先生有個齋號“雙蕉琴館”,就是說,他有兩張蕉葉琴。我認識他的時候,只剩下其中一張,另一張在戰亂中失去了,但他這個號一直沒改。那張蕉葉琴是淺紅色的,形體優美,斷紋也漂亮,琴體很輕,音量比較大,音質不是很好。他還有一張仲尼式的明琴,叫“驚濤”,黑漆色,琴體比蕉葉琴略大一點,聲音卻要小一些,音色也更好些。等后來有了比較,我覺得“驚濤”也不見得非常好——同樣是明琴,“驚濤”就不如我的“忘憂”。他一輩子經手過那么多琴,看過那么多琴,自己卻沒有得到特別好的,應該跟他的性格和觀念有關。我記得他工資是一百五十多塊,在當時是很高的。得到好琴,不僅要有錢,還要有機遇,他是既有經濟能力又有機遇的人,一個月的工資在當時買三張明琴是沒有問題的。而他不在這方面下功夫,只是彈琴。現在我翻看《操縵瑣記》,經常看到他品評見過的好琴,那時候我們聊天,偶爾也講講這方面的話題。另外,他有個簫,配琴的,我曾經聽他吹過。 張先生聊天,神采、動作是很鮮活的,有點像小孩。得意了,喜歡用手拍大腿,從右邊往左邊拍刮過去。他甚至會小孩子一樣說:“某某事情都做不成,殺我的頭!”如有琴人來拜訪他,彈彈琴,等這人走了,他就會評論這位彈琴人的彈奏特點、風格等等。有時候他覺得名不副實的彈琴人,也會對我說:“哎呀,嘖,這個人早就聽說了,琴不怎么樣啊!” (統籌:啟正 編輯:豌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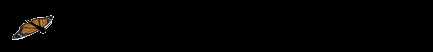

中華書局1912 2015-08-23 08:47:12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