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藏書票的故事:有書不讀,不如白紙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藏書票,是貼在書的首頁或扉頁上帶有藏書者姓名的小版畫。起源于15世紀下半葉的歐洲,至20世紀發展為繁盛時期,大約在20世紀20年代傳入中國。歐洲最早的藏書票是用木板刻制的,世界上有許多著名的版畫家都參與過藏書票的設計、創作。藏書票一般是邊長5-10厘米見方的版畫,上面除主圖案外,還有藏書者的姓名或別號、齋名等,國際上通行在票上寫上“EX—LIBRIS”(拉丁文),表示“屬于私人藏書”。 無相庵藏書 1988年10月我第一次到上海,便和好友秦賢次一起拜訪施蟄存先生。與施先生聊起來,仿佛打開塵封的往事。而我也有收獲,就是施先生送我當時采用肯特版畫、嵌上他姓氏的英文字母S而合成起來的自用藏書票。更有意思的是,上海的友人后來送我一冊施先生的藏書――葉芝的詩集《塔》,書封的內頁貼上“施蟄存無相庵藏書之券1945―1948”。 “無相庵”是施先生畢生使用的第三個書齋名,是他青年與中年階段用得較為長久的室名。根據他的說法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他不信佛教,卻從《阿含經》中受益良多。因為他認為《阿含經》里純樸的風格和大量譬喻,闡說佛法理念和佛化弟子的因緣故事,對當時社會、政治的生動記載,是文學性最強的佛經。所以施先生雖然以《金剛經》中的“無相”作為書齋名,實際上他之于佛教,應該只是“文人禪”而已。 有趣的是,當時施先生將藏書票翻譯成“藏書券”。票面的中央有航海的羅盤、沙漏、精裝書以及不知名的花草和建筑物,四周還圍上繁復的花草紋飾。可見當時他在抗戰勝利后,多么想抓緊時間,出國四處游學,補充多年被局限在孤島上的苦悶。真是一款有意思的藏書票。 萬卷書齋 1986年7月5日,戈寶權將他50年來精心收集和珍藏的兩萬冊中外文圖書,捐獻給家鄉江蘇省南京圖書館。該館為他的贈書,特辟了“戈寶權藏書室”,室名為錢君以篆文所書。比較特別的是,還設計了一款藏書票。票面上的“萬卷書齋”由黃苗子書寫,戈寶權的肖像則由小丁(即著名漫畫家丁聰)所畫,最下方的“戈寶權藏書”取自錢君的篆書。 眾所周知,黃苗子、丁聰和范用是一群在北京的時有往來的文友,戈寶權與范用則是有60個年頭交往的書友。范用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在北京舉辦過葉靈鳳收藏的藏書票展,所以這款藏書票出自范用的構思是可想而知的。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首度到東總布胡同拜訪范用先生,老先生知道我是個藏書票迷,除了拿出幾本葉靈鳳收藏的藏書票書刊,讓我大飽眼福外,更難得的是送我數十款藏書票,其中就有這款藏書票,票面上還依稀可見戈寶權的親筆簽名。真是一段值得令人回味的前塵往事。 冰心和她的貓 冰心是一位充滿了愛心、富于生活情趣的作家。生活中的她愛貓、愛孩子,更愛開玩笑,所以她的一生從小到老,永遠保持心胸不老,并且筆耕不停。每當她的至親好友,步入她的書齋兼臥房時,那只可愛的大白貓“咪咪”,也許正伏在書桌的右角,靜靜地看她在素箋上寫著什么。有時好客的“咪咪”,會突然跳上桌,趴在她和客人的中間,借機和她撒嬌。 或者像畫面上的這款藏書票,“咪咪”跑到書上,翹起尾巴,跟它熟悉的訪友表態,示意歡迎他們的來訪。它長了一身雪白的長毛,拖一條可愛的黑尾巴,背上有兩個黑點,冰心戲稱之為“鞭打繡球”。圖中生動地將“咪咪”的形象,以絹印版畫設計出來,柔和的色調頗能傳達它優雅的姿態。和冰心所寫的愛,乃離去情欲的愛,一種母性的憐憫、一種童的純潔,頗為匹配。 這款藏書票完成于1992年,作者林世榮,設計過程中作者曾數度征詢冰心在上海朋友的意見,并且數易其稿,終于完成這款精心制作的藏書票。 人生是一本大書 我剛對藏書票登堂入室的時候,就不知天高地厚,在《聯合文學》主編初安民的鼓勵下,為期一年,每期在該刊目錄之前的首頁介紹一款藏書票。陳雅丹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的,并蒙她惠賜這款藏書票。 畫面上酣然入睡的女孩,躺在“人生”這本大書上,做過無數彩色的夢,幻想著她未來的旅程。左手邊的小書,則是她童年時僅有的讀物,帶給她無數的愉悅。眼下,經過吳曉波敘說的《激蕩三十年》,早已經無法想象陳雅丹那個缺乏精神食糧的童年。如今雖然圖書充塞滿地,更是令人不堪回首。 陳雅丹,1942年生于廣西桂林,原籍浙江新昌。1965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擅長版畫與水墨畫,藏書票創作是她個人的雅好。藏書票之于她,可能是一面心靈的鏡子,或者是與友人一段肺腑的交談。她目前可能已經退休了。畫面上是她童年時代的寫照。 現在目睹這款藏書票,一轉眼又過去15年。人生有幾個15年。 有書不讀,不如白紙 鐘芳玲在臺北誠品書店舉辦《書天堂》新書發表會時,有一家人不但請她簽名,這家人的女孩還同時送她一款“有書不讀,不如白紙”的藏書票,熱心的她也幫我要了一張。票面中央除了有這句讀書格言外,在它的上方有國際藏書票聯合會規定的拉丁文“EX―LIBRIS”,在它們的上下各有一排四個“安琪藏書”。 我收到之后,越看越有趣。雖然它只是一個12歲小女生用計算機創作的藏書票,但是它已經具備藏書票規定的要素。我們研究和推廣藏書票的目的,并不是每個人都要像我一樣,“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去鉆研和著書立說,甚至花很多錢去收集那些名貴的藏書票。 最重要的是,要從中享受樂趣。就像歌德說:“‘美’需要助長,‘用’則會自我助長。”“美”的東西并非一定要據為己有,而且就像藏書票,我們更可以動手創作,貼在自己心愛的書上。 邪惡與幽默的對立 19世紀末,很少有人像比亞茲萊在短短25年的生命中,以黑白插畫留給世人無盡的藝術遺產。連年輕時的畢加索,也曾模仿過他的作品。比亞茲萊設計的插圖、海報與書籍封面,如今都已經成為收藏家的珍藏,在英國有一座他的紀念館。 同時,比亞茲萊設計的插圖偶爾也被朋友拿來制作成藏書票,并且成為藏書票迷的珍藏。畫面上是比亞茲萊流通最廣的藏書票,原來是他自己要用的,后來給他的朋友波利特使用。圖中,比亞茲萊以莎樂美造型畫的裸女,以面帶邪惡、內心捉摸不定的表情,斜視著畸形、滑稽的矮胖子,胖子的雙手頂著頭上滿盤盛裝的書籍。從黑白畫的角度來看,這是典型比亞茲萊式的邪惡與幽默的對立,從中我們可以領會到他藝術創作的天分,表現出世紀末頹廢的傾向和獨特的唯美氣氛。 我坐在書墳上 古代的人們對讀書人有種種謔稱,例如,讀書雖多,但不求甚解的,稱“書麓”;讀書多卻不能應用的,稱“書櫥”;看書多,家里藏書汗牛充棟的,稱“書城”;一生勤奮讀書,出門則藏書跟隨,終日手不釋卷,讀書所坐之處,四面書籍卷軸盈滿的,稱“書窟”。南宋詩人陸游在山陰家居時,建造一個書房,稱“書巢”;明代文人丘瓊勤奮好學,才思敏捷,故有“書柜”的美稱。 這些稱號都與書籍擺放的場所有關,從中延伸出它真正的含義,有褒有貶,還有自嘲。不過最慘的,恐怕就是“書墳”了吧。就像有人在床上堆滿了書,床下塞滿了書,周圍的書架擺滿了書,只容一個人走進這間臥房兼書房,那不叫書墳,叫什么?我很早就有這種危機意識,進入職場工作以后,就開始轉向收集藏書票。但是為了研究藏書票,又造成書滿為患、類似書墳的窘態。 所以當我看到芬格斯坦這款藏書票時,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仿佛它勾勒出了我的陳年往事。 《我的藏書票》/吳興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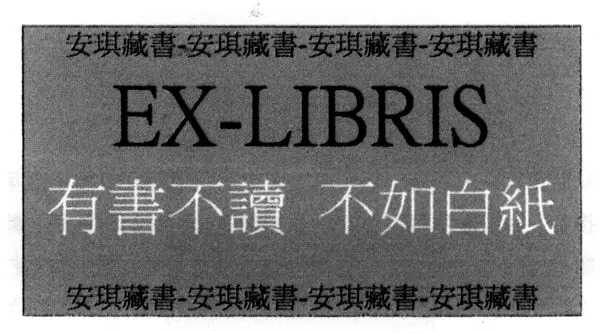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9:59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