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路遙:人要對自己殘酷一點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最涉小的作家常關注著成績和榮耀,最偉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創造和勞動。只有初戀般的熱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種事業。 平凡的世界 作者 | 路遙 路遙:中國當代作家,生于陜北清澗縣一個世代農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氣勢和史詩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現了改革時代中國城鄉的社會生活和人們思想情感的巨大變遷,該作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 有時要對自己殘酷一點。應該認識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嚴峻的牛馬般的勞動,無論作為作家還是作為一個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將終結。只有初戀般的熱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種事業。 在我的創作生活中,幾乎沒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從中午開始的。這是多年養是的習慣。我知道這習慣不好,也曾好多次試圖改正,但都沒有達到目的。這應驗了那句古老的話:積習難改。既然已經不能改正,索性也就聽之任之。在某些問題上,我是一個放任自流的人。 通常情況下,我都是在零晨兩點到三點左右入睡,有時甚至延伸到四到五點。天亮以后才睡覺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午飯前一個鐘頭起床,于是,早晨才算開始了。 午飯前這一小時非常忙亂。首先要接連抽三五支香煙。我工作時一天抽兩包煙,直抽得口腔舌頭發苦發麻,根本感覺不來煙味如何。有時思考或寫作特殊緊張之際,即是顧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燃的煙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幾支煙簡直是一種神仙般的享受。 用燙湯的水好好洗洗臉,緊接著喝一杯濃咖啡,證明自己同別人一樣擁有一個真正的早晨。這時,才徹底醒過來了。 午飯過后,幾乎立刻就撲到桌面上工作。我從來沒有午休的習慣,這一點像西方人。我甚至很不理解,我國政府規定了那么長的午睡時間。當想到大白天里正是日上中天的時候,我國十一億公民卻在同一時間都進入夢鄉,不免有某種荒誕之感。又想到這是一種傳統的民族習性,也屬“積習難攻”一類,也就像理解自己的“積習”一樣釋然了。 整個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時間,除過上廁所,幾乎在桌面上頭也不抬。直到吃晚飯,還會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飯后有一兩個小時的消閑時間,看中央電視臺半小時的新聞聯播,讀當天的主要報紙,這是一天中最為安逸的一刻。這時也不拒絕來訪。夜晚,當人們又一次又睡的時候,我的思緒再一次躍起來。如果下午沒完成當天的任務,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進入閱讀(同時交叉讀多種書),或者詳細考慮明天的工作內容以至全書各種各樣無窮無盡的問題,并隨手在紙上和各式專門的筆記本上記下要點以備日后進一步深思。這時間在好多情況下,思緒會離開作品,離開眼前的現實,穿過深沉寂靜的夜晚,穿過時間的隧道,漫無邊際地向四面八方流淌。人睡前無論如何要讀書,這是最好的安眠藥,直到睡著后書自動從手中脫離為止。 第二天午間醒來,就又是一個新的早晨了。 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寫作過程中,我的早晨都是這樣從中午開始的。對于我,對于這部書,這似乎也是一個象征。當生命進入正午的時候,工作卻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陽一般充滿青春的朝氣投身于其間。 小說《人生》發表這后,我的生活完全亂了套。無數的信件從全國四面八方蜂擁而來,來信的內容五花八門。除過談論閱讀小說后的感想和種種生活問題文學問題,許多人還把我當成了掌握人生奧妙的“導師”,紛紛向我求教:“人應該怎樣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規定我必須趕幾月幾日前寫信開導他們,否則就要死給你看。與此同時,陌生的登門拜訪者接踵而來,要和我討論或“切磋”各種問題。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亂中添忙。刊物約稿,許多劇團電視臺電影制片廠要改編作品,電報電話接連不斷,常常半夜三更把我從被窩晨驚醒。一年后,電影上映,全國輿論愈加沸騰,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沒了。另外,我已經成了“名人”,親戚朋友紛紛上門,不是要錢,就是讓我說情安排他們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僅腰纏萬貫,而且有權有勢,無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當時分文不帶而周游列國的文學浪人,衣衫襤褸,卻帶著一臉破敗的傲氣莊嚴地上門來讓我為他們開路費,以資助他們神圣的嗜好,這無異于趁火打劫。 也許當時好多人羨慕我的風光,但說實話,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條縫趕快鉆進去。 我深切地感到,盡管創造的過程無比艱辛而成功的結果無比榮耀;盡管一切艱辛都是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許在于創造的過程,而不在于那個結果。 我不能這樣生活了。我必須從自己編織的羅網中解稅出來。當然,我絕非圣人。我幾十年在饑寒、失誤、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長歷程中,苦苦追尋一種目標,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對我都至關重要。我為自己牛馬般的勞動得到某種回報而感動人生的溫馨。我不拒絕鮮花和紅地毯。但是,真誠地說,我絕不可能在這種過分戲劇化的生活中長期滿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種沉重。只有在無比沉重的勞動中,人才會活得更為充實。這是我的基本人生觀點。細細想想,迄今為止,我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寫《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歲的中篇處女作已獲得了全國第一屆優秀中篇小說獎,正是因為不滿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寫作中。為此,我準備了近兩年,思想和藝術考慮備受折磨;而終于穿過障礙進入實際表現的時候,精神真正達到了忘乎所以。記得近一個月里,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通,演更半夜在陜北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長犯了疑心,給縣委打電話,說這個青年人可能神經錯亂,怕要尋“無常”。縣委指示,那人在寫書,別驚動他(后來聽說的)。所有這一切難道不比眼前這種浮華的喧囂更讓人向往嗎?是的,只要不喪失遠大的使用感,或者說還保持著較為清醒的頭腦,就決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長期停泊在某個溫暖的港灣,應忘該重新揚起風帆,駛向生活的驚濤駭浪中,以領略其間的無限風光。人,不僅要戰勝失敗,而且還要超越勝利。 那么,我應該怎么辦。 有一點是肯定的,眼前這種紅火熱鬧的廣場式生活必須很快結束。即是變成一個純粹的農民,去農村種一年莊稼,也比這種狀況于我更為有利。我甚至認真地考慮過回家去幫父親種一年地。可是想想,這可能重新演變為一種新聞話題而使你不得安寧,索性作罷。 但是,我眼下已經有可能冷靜而清醒地對自己已有的創作作出檢討和反省了。換一個角度看,盡管我接連兩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人生》小說和電影都產生了廣泛影響。但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作家的勞動絕不僅是為了取悅于當代,而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的交待。如果為微小的收獲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種無價值的表現。最涉小的作家常關注著成績和榮耀,最偉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創造和勞動。勞動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標。人類史和文學史表明,偉大勞動和創造精神即使產生一些生活和藝術的斷章殘句,也是至為寶貴的。 勞動,這是作家無義反顧的唯一選擇。 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當時,已經有一種論斷,認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個高度。我承認,對于一個人來說,一生中可能只會有一個最為輝煌的瞬間——那就是他事業的頂點,正如跳高運動員,一生中只有一個高度是他的最高度,盡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躍無數次橫桿。就我來說,我又很難承認《人生》就是我的一個再也躍不過的橫桿。 在無數個焦慮而失眠的夜晚,我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種幾乎是純粹的渺茫之中,我倏然間想起已被時間的塵土埋蓋得很深很遠的一個早往年月的夢。也許是二十歲左右,記不清在什么情況下,很可能在故鄉寂靜的山間小路上行走的時候,或者在小縣城河邊面對悠悠流水靜思默想的時候,我曾經有過一個念頭:這一生如果要寫一本自己感動規模最大的書,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歲之前。我的心不由為此而顫粟。這也許是命運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議,我已經埋葬了多少“維特時期”的夢想,為什么唯有這個諾言此刻卻如此鮮活地來到心間? 幾乎在一剎那時,我便以極其嚴肅的態度面對這件事了。是的,任何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某種抱負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時期會有過許多理想、幻想、夢想,甚至妄想。這些玫瑰色的光環大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環境的變遷而消散得無蹤無影。但是,當一個人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備了某種實現雄心抱負的條件,早年間的夢幻就會被認真地提升到現實中并考察其真正復活的可能性。 經過初步激烈的思考和論證,一種頗為大膽的想法逐漸在心中形成。我為自己的想法感動吃驚。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為什么又不可能呢! 我決定要寫一部規模很大的書。 在我的想象中,未來的這部書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滿意的作品,也起碼應該是規模最大的作品。 說來有點玄,這個斷然的決定,起因卻是緣于少年時期一個偶然的夢想。其實,人和社會的許多重大變數,往往就緣于某種偶然而微小的因由。即使像二次世界大戰這樣驚心動魄的歷史大事變,起因卻也是在南斯拉夫的一條街蒼里一個人刺殺了另一個人。幻想容易,決斷也容易,真正要把幻想和決斷變為現實卻是無比困難。這是要在自己生活的平地上堆積起理想的大山。我所面臨的困難是多種多樣的。首先,我缺乏或者說根本沒有寫長卷作品的經驗。迄今為止,我最長的作品就是《人生》,也不過十三萬字,充其量是部篇幅較大的中型作品,即是這樣一部作品的寫作,我也感動如同陷入茫茫沼澤地而長時間不能自拔。如果是一部真正的長篇作品,甚至是長卷作品,我很難想象自己能否勝往這本屬巨人完成工作。是的,我已經有一些所謂的“寫作經驗”,但體會最深的倒不是歡樂,而是巨大的艱難和痛苦,每一次走向寫字臺,就好像被綁赴刑場;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場大病。人是有惰性屬性的動物,一旦過多地沉湎于溫柔之鄉,就會消弱重新投入風影的勇氣和力量。要從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氣氛中,再一次踏進冰天雪地去進行一次看不見前途的遠征,耳邊就不時響起退堂的鼓聲。 走向高山難,退回平地易。反過來說,就眼下的情況,要在文學界混一生也可以。新老同行中就能找到效仿的榜樣。常有的現象是,某些人因某篇作品所謂“打響”了,就坐享其成,甚至吃一輩子。而某些人一輩子沒寫什么也照樣在文學界或進而到政界去吃得有滋有味。可以不時亂七八糟寫點東西,證明自己還是作家,即使越寫越乏味,起碼告訴人們我還活著。到了晚年,只要身體允許,大小文學或非文學活動都積極參加,再給青年作者的文章寫點序或題個字,也就聊以自慰了。但是,對于一個作家,真正的不幸和痛苦也許莫過于此。我們常常看到的一種悲劇是,高官厚祿養尊處優以及追名逐利埋葬了多少富于創造力的生命。當然,有的人天性如此或對人生沒有反省的能力或根本不具有這種悟性,那就另當別論了。動搖是允許的,重要的是最后能不能戰勝自己。 退回去嗎?不能!前進固然艱難,且代價慘重,而退回去舒服,卻要吞咽人生的一劑致命的毒藥。 還是那句屬于自己的話:有時要對自己殘酷一點。應該認識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嚴峻的牛馬般的勞動,無論作為作家還是作為一個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將終結。 最后一條企圖逃避的路被堵死了。 我想起了沙漠。我要到那里去走一遭。 我對沙漠——確切的說,對故鄉毛烏素那里的大沙漠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或者說特殊的緣分。那是一塊進行人生禪悟的凈土。每當面臨命運的重大抉擇,尤其是面臨生活和精神的嚴重危機時,我都會不由自主地走向毛烏素大沙漠。 無邊的蒼茫,天邊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個星球。嘈雜和紛亂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聞天籟之聲。此間,你會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來觀照生命,觀照人類的歷史和現實。在這個孤寂而無聲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場景會無比開闊。你體會生命的意義也更會深刻。你感動人是這樣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議的巨大。你可能在這里迷路,但你也會廓清許多人生的迷津。在這單純的天地間,思維常常像洪水一樣泛濫。而最終又可能在這泛濫的思潮中流變出某種生活或事業的藍圖,甚至能明了這藍圖實施中的難點易點以及它們的總體進程。這時候,你該自動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紛擾的人間。你將會變成另外一個人,無所顧忌地去開拓生活的新疆界。現在,再一次身臨其境,我的心情仍然過去一樣激動。赤腳行走在空寂逶迤的沙漠之中,或者四肢大展仰臥于沙丘之上眼望高深莫測的天穹,對這神圣的大自然充滿虔誠的感恩之情。盡管我多少次來過這里接受精神的沐浴,但此行意義非同往常。雖然一切想法都在心中確定無疑,可是這個“朝拜”仍然是神圣而必須進行的。 在這里,我才清楚地認識到我將要進行的其實是一次命運的“賭博”(也許這個詞不恰當),而賭注則已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盡管我不會讓世俗觀念最后操縱我的意志,但如果說我在其間沒作任何世俗的考慮,那就是謊言。無疑,這部作品將耗時多年。這其間,我得在所謂的“文壇”上完全消失。我沒有才能在這樣一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還能像某些作家那樣不斷能制造出許多幕間小品以招引觀念的注意,我恐怕連寫一封信的興趣都不再會有。如果將來作品有某種程度的收獲,這還多少對拋灑的青春勢血有個慰藉。如果整個地失敗,那將意味著青春乃至生命的失敗。這是一個人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華,它的流失應該換取最豐碩的果實——可是怎么可能保證這一點呢!你別無選擇——這就是命運的題旨所在。正如一個農民春種夏耘。到頭一場災害顆粒無收,他也不會為此而將勞動永遠束之高閣;他第二年仍然會心平氣靜去春種夏耘而不管秋天的收成如何。那么,就讓人們忘記掉你吧,讓人們說你已經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樣從文學界消失,重返人民大眾的生活,成為他們間最普通的一員。要忘掉你寫過《人生》,忘掉你得過獎,忘掉榮譽,忘掉鮮花和紅地毯。從今往后你仍然一無所有,就像七歲時赤手空拳離開父母離開故鄉去尋找生存的道路。沙漠之行斬斷了我的過去,引導我重新走向明天。當我告別沙漠的時候,精神獲得了大解脫,大寧靜,如同修行的教徒絕斷紅塵告別溫暖的家園,開始餐風飲露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沙漠中最后的“誓師”保障了今后六個年頭無論多么艱難困苦,我都能矢志不移地堅持工作下去。 只有初戀般的熱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種事業。 本文選自《平凡的世界》,轉載請注明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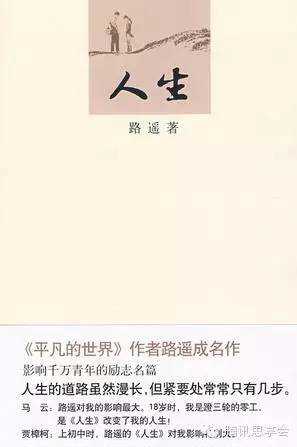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5:21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