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周末一讀】探求哲學“最重大”問題的意義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記得曾有人問到我“搞哲學搞的是哪一部分”,我當時無法回答,現在仍然不能很好地回答。我所關注并且一直為之不安的并不是“某一部分”的哲學問題,而是“搞哲學”這個問題。 探求哲學“最重大”問題的意義 作者 | 趙汀陽 在哲學的“知識”方面,我向來很后進。1978年考大學時我還不知道黑格爾是誰,盡管當時在中國文人眼里黑格爾是最偉大的哲學家。在哲學系讀書時,我甚至厭惡哲學,因為我感受不到哲學書所討論的那些“最大的”問題有什么重要性。開始我覺得錯誤可能在我,因為我知識貧乏。多年之后我終于堅信最大的問題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錯誤不再是我的而是哲學的。我感覺有了一種思想才能,可以用來破壞而后建設一個新的哲學概念。同時還體會到,智慧不可能通過知識去獲得。 在到北京上大學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廣東一個邊遠小城,那時即使不說是窮鄉僻壤,也是一處閉塞之地,諸如科學、人文思想、音樂、戲劇這些東西是絕對的遙遠,只能見到一些小說和圖片,好像這就是世界。小學和初中時我曾經決心要當畫家,還研究古詩詞想當詩人,倒不是因為有這些方面的才華——事實上我自己很快就發現不具有這些方面的才華——而是根本沒有別的天地可供發泄才華。同時也研究文學,糟糕的是,由于見不到別的文學研究,于是以為“紅學”是唯一的文學研究。我至今還打算堅持認為我在初中時的一個紅學見解是真正的“創見”,簡單地說就是認為高鶚的續作比曹雪芹關于結局的設想要高明得多,因為精神上的幻滅比事實上的家破人亡在悲劇性上要深刻得多,盡管家道復興富貴如初,但癡人奇情溫柔之鄉不復存在,這種無聊式的空蕩蕩才會使人有悲難言,而家破人亡只是一種常見的套路。大概如此,當然那時我不可能表達得這樣成熟。諸如此類五花八門的“創見”還有許多,但大多數都是荒謬的,當時畢竟思想水平很有限。家鄉的閉塞性顯然不利于知識的增長,記得剛到北京時曾驚訝地發現,所有人都知道一切事情,而我一切都不知道。不過,閉塞性很可能反而激發創造性,因為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想像。有一次李澤厚說到我以為考不上他的研究生,因為在答題時多半是胡說八道。李澤厚說他記不得是些什么樣的胡說,但記得很有“判斷力”,他解釋說就是能發現并抓住重要的問題。 現在想起來,我早就自發地思考過一些哲學問題,盡管在很長時間里不知道那些問題是“哲學的”。我曾與一個初中好友(他高中時就自殺了)整天討論生活的意義、幸福和愛情。這些討論肯定十分粗淺毫無條理,但也有一個額外的好處:我們毫無知識背景,沒有什么現成的傳統和理論可以利用,這樣反而能夠直接親臨問題本身。盡管這些討論沒有使我獲得任何一個清醒的結論,但很可能培養了一種我堅信是正確的思考習慣,即親臨問題。只有在能夠親臨問題的前提下,所有的傳統和理論才能被積極地利用,否則就只是一些堵塞思路的思想障礙。 大學給了我一個自學哲學的機會。大學課程多半是無聊的,但大學里人人都在思考,這是良好的自學環境。對于大多數學科來說,標準化的、按部就班的學習可能是合適的,但對于哲學(還有文學),標準化學習恐怕事倍功半。大學時代正值“開放”初期,大家思考的熱情極高,不過所談論的問題通常過于籠統含糊,對此我很迷惑也很不滿。當時有一陣子所謂的“真理標準”的討論,我隱約感覺到真理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而且,人們對真理的一些通常理解中暗含著嚴重的缺陷。一直到近兩年我才覺得終于看清了真理問題的一些要害,因此便開始表述一種新的真理理論。多少令人有些驚訝,當時還出現了“美學熱”,我也很有興趣。有個同學叫孫元寧,一個思想澄明的人,有一次給我了重要的啟示,他大概是這樣說的:我們不可能在對一種藝術無所了解時就說它是美的還是不美,例如一首搖滾歌曲(這一例子似乎不太恰當,但當時正聽著搖滾),我為什么覺得它好,我只是覺得它的確是一首搖滾,而且它和所聽過的大不一樣。我因此感覺到諸如“美”、“表現”、“意味”等問題根本說明不了任何問題。有趣的是數年后我讀到維特根斯坦也有類似見解,當然維特根斯坦的見解要深入得多。后來我把美學論點寫成一本書,但顯然有不少缺陷,已經遠不及我今天尚未表述的見解。 美學不是我的研究主題,后來我主要研究存在論、哲學邏輯和倫理學,在1990年前雖有各種進展,但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思路,盡管對現行的哲學操作非常不滿,但還不能設想出另一種哲學操作。多數哲學家都對我有所影響,但具體真實的生活、生活中周圍的人們以及其它非哲學領域的思想對我有更大的影響。專門的哲學家的偏執過火的追問往往引向一些大而無當的問題,好像能夠為哲學而哲學,而忘記了人們對哲學的真正需要和哲學的真正功能,哲學變成了一種脫離實際的文化慣性。那些非哲學的思想雖然在主題上與哲學無關,但在思想細節上卻富有啟示性。例如布勞維爾、康托、希爾伯特、哥德爾的一些數學或邏輯思想都曾使我受益。我還記得莫紹揆在一本介紹數理邏輯的書中關于函數的解釋使我茅塞頓開,確實如莫紹揆指出的,一般教科書講函數都含混不清,從中學以來我一直就搞不清楚。函數關系意味著一種最基本的思維方式,這些思想細節和哲學大大有關。 90年左右,我猛然意識到,現行哲學從思想方法到所思考的問題都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不良的哲學操作卻損害了哲學。使我不滿的已不再是哲學中某個具體理論觀點,而是哲學的運行方式。這要求一種整體性的改變的道理而不是某方面的修改。前不久看到維特根斯坦有一段話似乎可以用來表達這種整體性改變的道理,大意是這樣的:解決哲學問題就像開一個復雜的保險柜,只有當每道機關同時對上了,才能一下子打開門,一點一點打開是不可能的。當我意識到整體性改變的必要性,就不再就某個觀點斤斤計較,每個問題都不再僅僅屬于知識論還是倫理學或者美學,而是牽動著哲學整體。整體地改變哲學這一概念,這并不是我的一個私人愿望或興趣,而是思想的要求,是思想本身自然發展出來的需要,我們迫不得已面對它。這一經驗使我意識到:思想不能按照私人的興趣和要求,而必須按照思想自身的要求,否則所謂的思想必定弱化為一種文學類型或文化雜談感想。盡管思想永遠是為了人的,但卻不是用來感動人的,思想本身是冷酷無情的(有人曾把我的哲學理論描述為“思想謀殺”)。由于我的論述風格比較冷酷,因此有些人認為我的思想與分析哲學比較親近,其實恰好相反,在我看來,分析哲學毛病很多甚至是不可救藥的。我堅信我的思想是中國式的,當然是現代化了的中國思路。至于表述形式,僅僅是選擇了現代的風格。我近幾年的想法主要表述在《走出哲學的危機》和《論可能生活》兩本書以及一些論文中。 假如我關于哲學改革的設想是恰當的,那么,哲學會有什么樣的新面目?或者說,我希望我的設想能給哲學帶來什么后果? 人類觀念的主要形式是描述和理解,前者想說明某種東西“是”什么,后者想把某種東西“看作是”什么,由此分別形成知識和意見。哲學一直不能表明自身是知識還是意見,糟糕的是,哲學家們以為哲學或者是一種更高的知識或者是更高的意見。我希望人們意識到,根本不可能有哲學的知識或意見。假如哲學是知識,那么是多余的,因為在科學之外不再有什么有用的知識;假如哲學是意見,那么毫無特殊地位,因為它不可能比日常意見更重要,而且通常只不過是些貼滿了文化標簽的日常意見。哲學試圖制造出一些真理。真理不是知識,知識也絕不是真理。科學雖然是人類智力的頂峰之作,但卻不是真理,而是對世界的高效解釋。真理只屬于邏輯、數學和哲學。就是說,只有當思想的對象恰好是思想的創造作品時才會有真理,至于世界和歷史,我們永遠只能“在外”地進行解釋,說起來道理很簡單:只有我們的作品,我們才有全權斷言它。如果哲學是知識,那肯定是最差勁的知識;如果哲學是意見,那無疑是最差勁的宗教。從古希臘開始,西方哲學就猶豫于知識和意見之間,有趣的是中國哲學從來就沒有這類困惑,在中國,純粹的思想從來就不是知識也不是意見,而是“道理”,在我看來,“道理”就是哲學真理。這其中暗示著一種新的真理概念,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把它做成一個真理理論,但結論卻簡單得出奇:西方哲學錯誤地用知識論去解釋真理,其實x是真的、x是好的等等只是取值類型不同,并不存在所想像的更多的差別,至于x是真的或x是好的這些形式下的命題哪一個是真理則取決于是否有相應的充足斷言條件。我相信這一真理概念可以導致一些不尋常的結果,例如價值命題(尤其是倫理學命題)可以是真理。這正是中國式的哲學精神,在中國思想中,無論真偽善惡都有一個“是非”問題。知識在于發現,意見在于趣味,智慧在于創造。哲學的任務是制造真理。 我的另一個更有特色的理論是所謂“無立場”或“無觀點”的思想。這一理論往往令人反感,有不少人告訴我這一理論可能過火了,因為有悖常理。但我這一理論想表明的恰恰是哲學是一種反常思想,否則哲學就沒有價值。這種反常性只表現在思想方式上,因此我強調哲學的“平常心、異常思”。其實,“無立場”這一要求并非不允許我們從某種立場觀點去看事物,而是準備剝奪任何一種立場觀點的價值判定功能,也就是說,任一立場觀點都不是一個思想的證明,都不能表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好的。以往哲學都是有立場的,我敢說,對世界和生活的任何一種哲學的解釋,盡管有著嚇人的思想偽裝,但決不比任何一種拙劣的迷信更可靠。我們要求哲學表現出一種明顯的智慧之道,就像我們要求醫生對疾病有著明確的診治手段,我們決不希望醫生根據不同的“立場”把某種疾病說成是肺炎、腸炎和消化不良。一個哲學家,無論多么偉大,他至多有著更高明的思想操作,但絕不意味著他有著高于正常人的更有價值的立場、更值得贊嘆的感受、更值得模范的體會。每個人都有哲學立場觀點,哲學的立場觀點恰恰不屬于哲學,哲學必須退出哲學立場觀點而發展成為哲學的思想操作。在《論可能生活》一書中,我試圖以實踐的方式表明,在沒有預設的立場觀點的條件下,僅靠一些基本事實和純粹的思想技巧即能引出足以解釋倫理問題的原則。 由“無立場”這一哲學性質,我很自然地想到有必要設計一種新邏輯。對于人類思想來說,科學所能說明和證明的東西是有限的,邏輯(一般意義上的邏輯)的能力同樣是有限的。現代哲學特別是分析哲學對邏輯很迷信,其實邏輯只是思想的一項要求,它根本沒有充足的能力去說明思想的恰當性,甚至邏輯本身就需要被說明和解釋。邏輯學家通常只是關心邏輯系統的嚴密和完備,但卻幾乎不能說明邏輯。我希望有一種新邏輯或者說思想自身解釋的方式,它至少能夠表明:(1)邏輯操作的真正性質是什么樣的,這是從思想對邏輯的要求去反思邏輯而不是按照邏輯去解釋思想;(2)人類思想中各種基本原則怎樣才是恰當的。思想的基本原則無論是屬于哪個領域的基本原則都正是科學和邏輯所不能說明的,人類一直不能做到這一項自身解釋。把思想的基本原則說成是先驗的或自明的,這實際上并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基本原則必須能夠以某種思想操作模型去說明。關于新邏輯,我自己心里也不十分明確,我只是意識到了這是思想自身的一項要求。我猜想思想的自身解釋首先需要建立一種新的語言理論,它與分析哲學所關心的語言問題和語法結構完全不同。 按照我對“哲學”這一概念的改革,哲學的問題和思想結構都有著很大的變化。哲學問題不再是關于世界而是關于觀念界的問題,哲學問題的意義不再是引出某種觀點而是導致某種思想或行為操作。哲學不再是關于事物的描述和理解,而是關于行動的決定和決斷。一個事物的存在和本質不是問題,怎樣使用這個事物才是問題。哲學一直都過于注重名詞或主詞,而我堅信首先必須關注動詞或謂詞,并且永遠使關于主詞和名詞的問題服從于關于謂詞和動詞的思考。不要總向別人宣揚你的理解、體會和觀點,任何一個哲學家或者任何人的理解和體會都不可能比任何一個別人的理解體會更有價值,因為沒有一個人需要別人的體會(除非是日常生活的交流)。別人只需要有人能提供一些有效的操作。無論是關于真理和意義還是關于幸福和公正,我都只想指出一些有效的操作。盡管我的表述是現代式的,但精神實質卻是中國式的。在中國思想中,諸如“道”“仁”等最基本的概念從來就不是意味著某種事物或性質,而意味著某種做法。 如果我是對的,哲學將有一種新結構。首先將取消知識論,傳統意義上的存在論也不再存在。這是我的所謂“元觀念學”或“觀念存在論”的兩個基本后果。哲學的新結構將以倫理學和思想操作原理為主題。倫理學是人類全部生活問題的極端思考;思想操作原理是人類全部思想問題的極端思考(包括邏輯基礎、數學基礎、語言理論甚至藝術理論)。 我在思想上的各種設想從來都沒有那么圓熟和系統化,只是一些思想冒險和偵察。就是這樣。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哲思學意”,轉載請注明來源。
▲電視劇《紅樓夢》劇照
▲剛剛改革開放后的大學生形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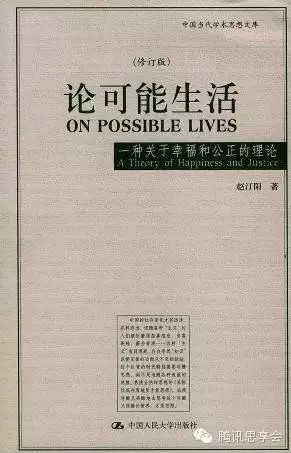
▲《論可能社會》圖書封面,趙汀陽著
▲趙汀陽講座近照
騰訊思享會 趙汀陽 2015-08-23 08:55:10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