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精英辦公桌殺人者
 |
>>>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 簡體 傳統 |
撰文:邁克爾·曼(Michael Mann) 翻譯:嚴春松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歷史社會學家邁克爾·曼在《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一書中首次揭露:為何殘忍的種族清洗是近代產物。無論是那些最駭人聽聞的事件——殖民主義的種族滅絕、亞美尼亞、納粹大屠殺、柬埔寨、南斯拉夫、盧旺達,還是那些殘酷程度稍輕的案例——近代早期的歐洲、當代印度、印度尼西亞,它們都是“民主的陰暗面”。 當同一片領土上,兩個對立的種族民族主義組織都聲稱自己擁有國家主權時,危險產生了;當弱勢的一方由于外部的支援而不愿屈服、選擇戰斗,或者強勢的一方認為自己能夠驟然展開銳不可當的武力行動時,沖突便升級了……行動升級并不只是“邪惡的精英”或者“未開化的民族”的杰作,它同樣產生于領袖、激進分子以及種族民族主義的“核心擁護者”之間的復雜互動。 曼的解讀聚焦于社會中的政治權力關系,令人信服地闡明了種族清洗的源頭及升級過程,有助于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以下文字節選自該書第九章:“納粹III:種族滅絕事業”。 事業路線之一:精英辦公桌殺人者 絕大多數帝國中央保安局成員不習慣于暴力。他們是同一代人,出生于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太年輕而未能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一帆風順,受過高等教育,三分之二有大學學位,三分之一擁有博士學位。絕大多數在大學時就曾是納粹或激進右翼分子,1933年前加入納粹。到30年代中期他們準備按照納粹種族—國家學說重新改造世界。他們知道需要采取行動,當時機到來時他們極少有人退縮(赫爾伯特,2000:26—27;懷爾德特,2002)。 阿道夫·艾希曼是以善于解決問題而著稱的人。他監督將納粹、軍隊及平民管理機構與死亡集中營聯系在一起的驅逐手段。他在耶路撒冷接受審訊時,精神病專家說他是模范丈夫——“在考查過他之后,我覺得他比我更正常”,有個人這樣說。他出生在萊茵蘭德,八歲時母親去世,全家搬到了奧地利。他在初中讀書期間以及之后一段時間里做銷售員,表現都較一般。1932年他加入了奧地利納粹黨,當時26歲;1934年,在那段非法時期,他聽從朋友卡滕布倫納的建議加入了黨衛軍。他當時對加入黨衛軍給出的理由是不公正的《凡爾賽和約》和大規模失業,但是事業受挫其實也是原因。1934年他經訓練成為達豪集中營的一名中士,次年進入黨衛隊保安處猶太部,在此他成為猶太復國主義專家。他把自己描述為“不感情用事和客觀的”人。對阿倫特(1965)來說,他是“平庸之惡”的縮影(一個她后來開始后悔使用的詞)。她覺得從道義上他“從未認識到他是在做什么”。這不是真的。艾希曼反猶非常堅決,他對猶太問題以及它的多種解決方案的專業業務知識已使得他做好了接受任何考驗的準備。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赫斯(1978:105)回想起他們戰時的談話: 即使是在我們倆獨處,隨意喝著什么,能充分放開情懷的時候,還是可以看出他老在思忖如何把每一個他能逮住的猶太人都滅掉。我們必須棄絕憐憫,不帶任何感情,盡可能快地完成這種根除。任何妥協,哪怕是最微小的,也必定將在以后使我們付出慘痛的代價。(赫斯等,1987:105) 他一次次告訴朋友,猶太人除了做勞工別無任何價值——而其中僅20%—25%的人能從事艱苦工作。迪特爾·威斯里舍尼(見后)說: 他不是不道德,他是根本沒有是非,一副徹底的冷漠無情的樣子。1945年2月他對我說——其時我們正在談論關于輸了245戰爭之后我們的命運:“當我躍入墳墓時我會哈哈大笑,就因為我殺掉了500萬個猶太人時的那種感受。那能給我很大的滿足和自得。”(戰犯審判,1946:第8卷) “冰冷”(Ice cold)意味著冷酷無情,不是置身事外。只有他在法庭上的技巧是平庸的,老是想開脫責任,不承認他發出過的命令。但他本人經常采取主動。他反對驅逐塞爾維亞猶太人,一位同事記在議事錄上,“艾希曼提議開槍射擊”。1942年艾希曼反對把猶太人從匈牙利驅逐出去。他說,最好,等到70萬名匈牙利猶太人能夠一次性全處理掉。他的建議兩次都被采納。這不是一種受規則支配的官僚政治:它是不固定的,允許官員往激進的方向進行創新。艾希曼的邪惡既不是不加思考,也不是平庸,而是革新性的、冷酷無情的和意識形態的(洛索威克持一致看法,2000)。 我跟蹤了往單一國家方向驅逐的行動過程。與艾希曼緊密合作驅逐匈牙利猶太人的是兩個有特殊背景的納粹。外交部高級代表叫艾德蒙德·費森邁耶,一個來自下法蘭柯尼亞(巴伐利亞州)的天主教徒。他曾是經濟學講師和成功的商人。作為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1932年他投向納粹黨。從1933起,黨衛軍為他的外交生涯提供資助。他晉升為黨衛軍中的準將,在說服匈牙利政府支持大規模驅逐中起了關鍵作用。他寫道:“猶太人是頭號敵人;110萬的猶太人,意義等同于數量有如布爾什維克先鋒隊員的陰謀家。”黨衛軍保安處頭號人物是奧托·溫克爾曼中將,出生于霍爾茨維格—霍爾斯坦,一名城市官員的兒子。在還是學生時,他就參加了1923年在魯爾地區對法國人的戰斗,結果被關押。作為一名保守派民族主義者,在1932年28歲時他轉向納粹黨。迪特爾·威斯里舍尼在“猶太人對外移民”局匈牙利司工作。他出生于1911年,22歲加入納粹黨,23歲加入黨衛軍和黨衛隊保安處。 他們的員工——如士兵伯格、格雷爾、亨謝、克魯邁、諾瓦克和斯伯林茨——是一直伴隨自由軍團或具有在德國或奧地利的巷戰經歷的老的或年輕納粹(克魯邁是個例外,僅到30年代中期才參加民族主義的繼而納粹的前線組織)。匈牙利驅逐行動被有意交付給可靠的人安排處理——因為他們全部在被占領國。這些是意識形態納粹,有事業前程是他們的獎賞。就像對集中營中的上層精英一樣,他們的目的與效率更容易從一個系統性的嚴格的意識形態中產生:追求“道德”清洗。這最終意味著不放過一個猶太人或布爾什維克。正如洛索威克(2000:8)所說,這是一個執行世界歷史任務的精英群體,意識形態上的效率專家,不是平庸的官僚。他們完全知道他們在干什么,直至最后一滴血。 被占領領土的長官和警長監督著在實地進行的殺戮。他們是兇狠的納粹,經常在政變發生前已富于巷戰經驗。與辦公桌殺手不同,他們親眼目睹和參與了殺人。他們慷慨激昂地宣揚一套赤裸裸的種族主義思想:“我們是優越民族,我們當中最低級的德國人也246比當地人口在種族上和在生物學上珍貴1000倍。”厄恩斯特·科克來自魯爾,是一名鐵路職員,因早期從事政治活動而被解雇。在20年代末期做了東普魯士的地方長官之后,他成了烏克蘭的帝國專員。“我對猶太人一無所求,除了讓他們消失。”來自巴登的漢斯·弗蘭克說。他是一名自由軍團老兵,一名納粹黨的律師,是當時帝國的司法部長和波蘭的最高行政長官。約瑟夫·伯克爾態度較為猶豫。他來自萊茵蘭—普法爾茨州,是一名手工業者的兒子,一名來自自由軍團的老兵,做過老師,在20年代末期成為一名黨內官員。他是一名保守的、熱愛秩序的納粹。1938年他是維也納的地方長官,在此他試圖抑制針對猶太人的野蠻搶劫與暴力。但當被告知希特勒支持此項行動時,他改變了觀念。他開始為元首工作。 東部警察指揮官中的老前輩是馮·丹姆·埃里克·巴赫-齊烈夫斯基,出生于波美拉尼亞的一個容克軍事家庭。他參加了“一戰”,然后服役于自由軍團和魏瑪軍隊。受希特勒影響,他辭去了委任,1930年加入了納粹黨,時年31歲,次年加入黨衛軍。作為一名12年的納粹帝國議會代表,羅姆清洗及黨衛軍和蓋世太保部隊的指揮官,他是希特勒的愛將,因“將共產黨反動派徹底擊垮”受到希特勒的贊揚。在一次特別行動隊完成任務之后他吹噓說:“愛沙尼亞沒剩下一個猶太人。”后來他又清洗了華沙猶太人居住區。 但他也有疑慮。1941年希姆萊去觀看一次特別行動隊清洗行動。因明顯緊張,他往后退縮,在每顆子彈打出的時候避開希姆萊的注視。射擊結束后,巴赫-齊烈夫斯基袒露了自己忐忑的心情,說: 元首,那些只是一百次(殺戮)……看看這個突擊隊中的士兵的眼睛,他們是怎樣地在深深發抖!這些人的余生算是結束了。我們在這里訓練什么樣的跟隨者?要么是神經病,要么是野蠻人! 極少有高級納粹在經歷殺戮時沒有道德上的猶疑。大多數人試圖將他們自己放在一個據稱是更高的道德目的之下。伯恩(1986)將這歸于嚴格的軍國主義熏陶、戰爭經驗、感情上往國家社會主義的轉向,以及對希特勒的極端服從。但是服從希特勒給了他們一種理想主義意識,個人的感情已服從于共同的事業。這類扭曲的理想主義在受過高等教育的施害人當中很普遍。當其他動機都不起作用的時候,意識形態的力量幫助了施害人將任務堅持到底。 非納粹機構也參加了合謀。沒有文職部門,幾乎什么事也完成不了。極少有文職官員有任何暴力或狂熱主義歷史。在外交部,布朗寧(1978)指出了兩類參加合謀的官員。第一類是1933年之前以及加入外交部之前具有知識背景的納粹成員。路德出生于柏林,一個高級文職官員的兒子。參加戰爭之后,他開了一家家具248進出口公司。1932年3月37歲時他加入納粹黨和黨衛軍,但這時他已經認識了許多納粹,還是里賓特洛甫的朋友。他很快成為了一名納粹柏林城市市政會委員。布朗寧稱他是“一個與道德無關的權力技師”,但這不是很恰當。他在成為職業外交官之前是職業納粹,只是在1936年進入外交部,然后很快得到晉升。 布朗寧的第二類人員是單一的野心家或追名逐利之輩,在政變后加入納粹黨,屬于見風使舵的納粹。他們包括了像奧托·馮·諾伊拉特那樣的貴族保守派外交官和像弗朗茲·拉德梅克那樣向上流動的男人,后者是一名來自梅克倫堡的鐵路工程師的兒子,到1933年才加入納粹黨,憑自己艱苦努力才進入猶太人事務部工作。布朗寧認為這些人比艾希曼更好地展現了平庸之惡。然而絕大多數是來自軍事和文職官員背景,而整個部門中滲透了反猶主義的保守的民族主義。拉德梅克堅信科學的種族主義——這是他能幫助起草馬達加斯加計劃和最后解決方案的主要資格。在我的樣本中,幾乎所有的文職官員——相較于很少的商人——都被吸收成為納粹。但是他們的納粹意識形態極少是用赤裸裸的言詞表達的,更少采用暴力方式。相反,它在他們所在的比較威權主義的文職部門中的職業經驗中獲得了反響。 1942年在萬塞召開的臭名昭著的副部長級會議奠定了在黨衛軍與文職部門之間執行最后解決方案所需要的合作基礎。納粹領袖原以為文職部門會有不同意見,然而一切進行順利。這很可能是因為除了克里青格(一個來自波蘭的德裔)之外的所有參與者都是老納粹。絕大部分討論與猶太人與基督教徒之間異族通婚的技術問題有關。一個半小時之后會議結束,繼而是喝茶休息,然后是午飯時間。最后解決方案的消息通過各個部門向外擴散,沒有引起很大騷動(希爾伯格,1978:264—265)。一味追名逐利的做法現在讓大家共同行動起來。高級官員担心他們會失去影響,需要他們所在的部門設計殺戮方案,而中層官員可以通過去到處涌現的猶太人司工作來推進他們自己的事業。財政局制定被驅逐者財產清單,然后把它們交給稅務局,勞動局收集工作手冊,房產局處理空置房屋,而國家鐵路部門修建通往集中營的鐵路并運送囚徒。 實際上這些人中誰也沒有殺人,也很少有過暴力歷史。布朗寧(1978)說他們將“一種去個性化的行政操作模式”、“一個政府階層的組織性成就”和“意識形態的灌輸”結合在了一起。但是他們以前的右翼意識形態思想相對較容易地變成了一種國家主權論的納粹主義,給予他們的追名逐利做法以一種原則性的色彩。官僚政治是遠離了殺戮的文職部門領域進行種族滅絕的手段,而納粹意識形態的響應給出了目的。繼續向東,兩者的結合顯得更加地迫不及待。文職官員知道他們的249意識形態實際上意味著什么,但是他們的一味追逐名利也更加赤裸裸。被派往波蘭和俄國工作的差使不受歡迎,并且人們經常是因為失業,甚至有犯罪活動才去的。穆夏爾(1999)認為這些官員貪污腐敗,公開地顯露種族主義傾向,試圖通過謀殺的熱情來救贖他們自己,恢復他們的事業前程。 產業界的情況不一樣。我在《法西斯主義者》中強調資本與勞動力都不屬于納粹核心擁護者,很少商人是意識形態納粹,盡管許多人在1933年之后趕浪潮加入了納粹。他們開辦奴隸勞力工廠,但不是為了利潤。幾乎所有人都成了同謀,因為隨著戰爭的進程,勞動短缺成為燃眉之急。有納粹關系的產業主義者,如波西亞,通過游說將囚徒作為勞力——先是西歐人,然后是斯拉夫人,最后是猶太人。到1942年年末,三分之一的德國勞動力是奴隸。他們的待遇相差很大。一些猶太人受到很好對待,比其他工廠里的法國或荷蘭勞力的待遇要好。然而法本化學工業公司(IG Farben)的經理吩咐替換患了病的勞動者,同時心里知道他們之后會被殺掉,而管理者定期地進入集中營挑選勞動力,斯特雷德說(1999)。 甚至在為數不多的被控告犯有戰爭罪的產業主義者和管理者當中也極少有人在1933年之前加入納粹黨。古斯塔夫·克魯普“榨干了”成千上萬的俄國人和猶太奴隸勞動力,所以他被免除了繼承稅,但是他從未加入納粹黨。庫爾特·施羅德和弗里德里克·弗利克從1932年起曾幫助資助了該黨,然而弗利克給予其他右翼黨更多,并只到1937年才加入納粹黨。施羅德1933年加入納粹黨。甚至是來自波蘭的失去領土上的“無恥和殘忍”的埃里克·迪特里希——他為他的企業從當地城市貧民窟招收工人,同時將孱弱者交給蓋世太保槍決——也是在1935年左右才入黨。產業主義者和金融家也采取贏利的政府的經濟立場,經常與黨衛軍密切合作。銀行經理漢斯·菲施博克是德奧合作后的奧地利內閣成員,然后去幫助管理荷蘭經濟。他是右派,盡管只到1940年才成為一名正式納粹,此時他得到了黨衛軍上尉的名譽軍銜。在德國資本家中我們距真正的平庸最近——大規模屠殺成為了現代社會中某種已被制度化和具有合理性的事物的副產品:從最小的成本中榨取最大的利潤。因為自由勞力供應短缺,價格昂貴,資本家樂得使用奴隸。當然,資本家、管理者甚至工頭不是一定要去殺人。他們把奴隸移交給黨衛軍,然后就試圖把他們全忘掉。他們主要是殺戮行為的物質主義同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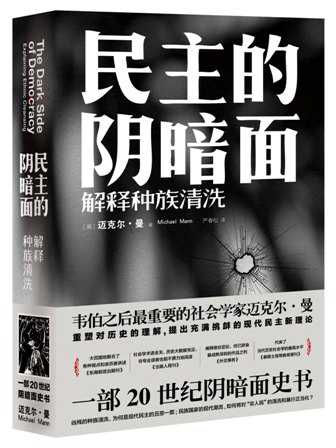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56:39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