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張新穎:沈從文的世界不拒絕任何人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新京報書評周刊微信ID:ibookreview 『與97000位智慧型微友同路同行』 ◎張新穎:沈從文的文學世界不拒絕任何人 文/新京報記者 柏琳 來源:2014年7月19日《新京報》(此為訪談完整版) 文學批評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在大學里開設有“沈從文精讀”、“中國新詩導讀”等課程,沈從文研究正是張新穎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成果最為豐碩的領域,他還撰寫了一系列當代文學批評和隨筆。張新穎1985年起就開始閱讀沈從文,如今,其“十六年磨一劍”的著作《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得見天光,借此契機,這個在沈從文的世界中久久徘徊不愿離開的人,終于可以坐下來,談談深埋心底的沈從文,聊聊沈從文以外的人和事。 ▲《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 作者: 張新穎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年6月 “真的歷史是一條河”讓我對沈從文的人生有了一個基本理解 新京報:很多人都說你已經是一個沈從文研究專家,您怎么看待這種評價? 張新穎:我實事求是地認為,我不是專家。你要讀懂一本書的話,可能需要讀很多本書之后才行,反之,你想讀懂很多本書,則要通過讀懂一本一本的書才行。我不是一個(研究沈從文的)專家,這帶給我的好處是,我不會把視線局限于這個單一領域。 新京報:這本大部頭的《沈從文的后半生》在學術界頗受好評,據說這本書花費了您16年的心血? 張新穎:說我花了16年寫成這本書,這種說法有點夸張,我并不是16年中都在干這一件事。1985年我開始讀沈從文,但并未有寫作想法。1992年,我讀了沈從文的家屬整理發表的《湘行書簡》——沈從文1934年從北平返回家鄉,在湘西的一條河流上給張兆和寫的一封封長信——我的感受無從言表,感覺必須寫一寫沈從文了。1997年,我寫出關于沈從文的第一篇文章——《論沈從文:從1949年起》,2002年底《沈從文全集》出版,32卷,一千多萬字,其中四百萬字生前沒有發表過,這四百萬字中的大部分又是1949年以來所寫的——讀完這些,我產生出強烈的寫沈從文后半生的沖動。2005年我開始著手,但只寫了一萬多字,就因長期面對電腦而患了眼疾,便無法繼續了。后來眼睛恢復了,但是被很多事情牽絆,寫這本傳記的事情便一拖再拖,成了我的心病。于是我在2012年秋天重新開始寫,這期間的過程很順利,因為材料已經在心里滾瓜爛熟,真正的寫作過程只有一年。 新京報:《湘行書簡》可以說是你研究沈從文的一個轉折點嗎?據說,你讀到他1934年1月18日下午寫下的那段文字,那段徹悟“真的歷史是一條河”,才感覺自己終于真正走進了沈從文的世界。你能談一談“真的歷史是一條河”為何觸發了你? 張新穎:《湘行書簡》對我來說是一個“機緣”。它本來就是沈從文在一條河上寫的東西,“真的歷史是一條河”,普通讀者可能會把它當成自然景物描寫,但其實這條河既是一條自然的河流,但人在這條河上生活,有船夫、有船娘……它和人的勞動、日常生活都連在一起,所以它又是一條“人”的河流。我從這里終于理解了沈從文到底關心的是什么。他關心的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勞動、創作和智慧這些東西。這句話構成了我對沈從文人生的一個基本理解,以及他后半生為何鐘情于雜文物的內心驅動力——那種對普通人所創造的歷史的深深的折服。 沈從文的文學世界不拒絕任何人 新京報:大眾可能只是會覺得沈從文后半生開始搞文物,由于政治或是命運里的無奈。你想通過這本傳記告訴讀者什么別的內容嗎? 張新穎:大眾對于沈從文的印象,可能會比較籠統,只知道他后半生開始搞文物研究,期間受過很多苦等等,對他的認識可能停留在對其命運的感慨上。而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沈從文后半生的“籠統”說清楚,所以我那么在意具體的事件和細節,為的就是清晰呈現他后半生的完整狀態。此外,我覺得,對一個人的了解,單單停留在對他命運的感慨上,這很不夠。有一些人會認為,沈從文很會明哲保身,建國以后他找了一個不為人注意的小角落(雜文物研究)藏起來“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是這樣的,我要寫的是,在這樣一個困難的環境里,他仍然要去做出一番事業的決心。 新京報:沈從文的文學過去了這么多年,為什么還有強盛的生命力? 張新穎:沈從文的文學世界能夠貼近日常生活,貼近普通人的真情實感,他的文學不挑選讀者。有的文學是挑選讀者的,比如一些專業的文學理論批評的書籍,只有學者才會閱讀。但是沈從文的書,無論你是學化學還是學數學的,你不一定完全了解沈從文,或者只看過一篇文章,但是也會非常喜歡,這就是說沈從文的文學世界不拒絕任何人。當一種文學開始挑選讀者的時候,它就把自己變小了。沈從文的文學不排斥普通的讀者,這就是他的魅力。 再者,如果把歷史時段拉長到五百年以后,再來寫中國文學史,根本不會寫到那么多作家。時間自動就把那些不夠優質的部分過濾了。有的作家被過濾,有的作家在時間的過濾中反而凸顯了出來。作家的價值,在時間過濾作用下,終會顯露。 新京報:《沈從文的后半生》這本傳記有個特點,“追求盡可能直接引述沈從文自己的文字”,你“更愿意看到傳主自己直接表達”,但你自己也在“說明”中提到,“這樣寫作有特別方便之處,但也有格外困難的地方”,這個“困難”指的什么? 張新穎:困難的地方在于,一個普通的讀者閱讀這本書時,需要不斷地在不同的敘述視角之間轉換,才看到立傳者說的話,下一句突然出現引號里的內容,再下一句又蹦出一段既非沈從文又非寫作者的第三人的引述,這樣來回的跳躍造成不流暢的感覺,帶來閱讀的障礙感。如果我用寫作者的第一人稱敘述,把直接引語轉化為間接引語,其實不難,但我很不愿意這么做。任何的轉化,哪怕再流暢也不能保證信息不扭曲、不流失。 ▲沈從文手繪圖 對愛好的東西存敬畏心,不要輕易涉足 新京報:由于一直以來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你在《迷戀記》的《小引》里把自己對外國文學的長期迷戀比作蜻蜓點水,自足于一種長期愛好者的狀態,在《迷戀記》里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大段的引文,而在《沈從文的后半生》中,“追求盡可能直接引述沈從文自己的文字”,這些都可看出你對引文對于寫作和閱讀的作用十分看重,可以談談原因嗎? 張新穎:(笑)我長得比較矮,習慣于從矮的角度看待事物。我們以往理解的研究者,往往站在一個“自以為”有高度的地方看待研究對象,用一種俯視或者說全景式的角度展開評論,或者是一種平等的角度和研究對象對話,這樣的研究者很害怕在自己的身影在書中被淹沒,顯示不出自己的才華、觀點。我不在乎這些,我本來就不具備這些,我不想在寫作中把自己凸顯出來,讓人看見我的影子。更誠懇地說,即使在文本中,我沒有直接“跳出來”,但在一個好讀者那里,他會強烈地感覺到我的存在,而不用我自己去強調。 新京報:你身為文學評論家,為何對于“引”的重視超過對“評”的重視? 張新穎:我之所以對外國文學采取多“引”少“評”的方式,是因為我堅持要對每個專業之間的差異保持足夠的尊重之心。一個人不能變成一個什么都懂,什么都談的人。我那么熱愛外國文學,所讀之書的數量甚至已經超過讀專業書的數量,但它確實不是我的專業,看待它的方式就不夠深入,所以,用“愛好者”這個詞形容我對外國文學的感情,最為恰當。“愛好者”這個身份可能會有局限,但也會有好處——一個愛好者看待問題的特殊視角,有時會比專家更有啟發性。我始終堅持,要對愛好的東西有敬畏之心,不要輕易去涉足。 新京報:你曾專文論述“中國當代文學中沈從文傳統的回響”,這種深遠影響甚至輻射到侯孝賢和賈樟柯等兩岸電影導演,能否具體談一下這種影響? 張新穎:侯孝賢在1983年拍《風柜來的人》這部電影前,已經有了很不錯的兩三部作品,但是他拍電影的態度是一種原始沖動式的方式——想說什么就拍什么。但在拍《風柜來的人》時,楊德昌等一群人從美國學習回來,告訴他,拍電影需要有一種“自覺”的意識。侯孝賢就很苦惱,他雖不太理解這種“自覺”,但也意識到原始沖動式的方式(拍電影)已經走到困境,這個時候朱天文(《風柜來的人》編劇)給了他一本《從文自傳》,他看完后恍然大悟,這種影響不是簡單的字詞句上的細節影響,沈從文給了侯孝賢一個觀看世界、觀看人生的全新角度,就像是攝影機的鏡頭。這種影響是根本性的,在《風》以及后來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見侯孝賢闡釋暴力、呈現普通人的生活都很有沈從文的痕跡。他特別強調,無論這個世界有多么殘暴,多么不仁義,在太陽底下你總是會感受到人和人之間真誠、樸素、溫暖的情感。你不會斤斤計較于永遠的暴力和黑暗,因為你關注了永恒存在的一種美,這樣一來,整個世界就拉開了。 后來的侯孝賢總是反復談論沈從文,此時他正好處在創作的轉折點上,需要確立其“自覺”拍電影的意識。沈從文的文學對侯孝賢的影響,是幫助其實現了“自覺”拍電影的方法、觀念和世界觀。楊德昌這批從美國學習回來的人所說的“自覺”,更多帶有學院派電影理論啟發的成分,而沈從文啟發給侯孝賢的“自覺”,是教你從自己的經驗來找看待世界的方法,堅持忠于自己的個人經驗。 新京報:那賈樟柯呢?賈樟柯為什么看沈從文的書? 張新穎:賈樟柯大概是上世紀90年代初在北京電影學院看到《風柜來的人》這部電影,他當時覺得很奇怪,為何侯孝賢講臺灣小青年的故事和自己家鄉小青年的故事如此相似?他為了弄明白,找來侯孝賢很多作品看,他發現侯孝賢總是在談沈從文,賈樟柯是個聰明人,于是也決定好好閱讀沈從文。于是,賈樟柯早期的作品如《站臺》、《小武》等,其中對地方、對鄉土人事的處理,帶上了非常強烈的沈從文印記。賈樟柯最近的一部作品《天注定》,我觀看以后特別強烈地想起沈從文。沈從文在40年代寫《長河》,寫現代“來了”之后的種種情形——家鄉在時代壓力下發生巨大的變化。他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說,“我要寫這樣一些人,他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變,如何變成另外一種人”,而《天注定》不就是想呈現人如何變成另一種極端的形式嗎?這種對暴力、對極端性的處理,在現代作家中,沈從文是處理得最多的。” 新京報:聽說你年輕時是個文藝青年,喜歡搖滾,而且架子鼓打得不錯? 張新穎:架子鼓我的確會打,但其實是玩票的性質,喜歡搖滾也是年輕時候的故事了。我喜歡崔健,但是對搖滾的了解也就到張楚為止,之后就完全不了解了。搖滾的意義在中國和在西方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崔健出現時,他的意義不僅僅音樂,他更是一種社會文化反抗的標志,但到后來(搖滾)概念逐漸縮小了,完全變成了流行音樂領域的事情,我對它的關注也就少了。 ◇記者手記 2014年7月14日之前,我與文學評論家張新穎素未謀面。作為一個文學評論的愛好者,我關注張老師有幾年了,除了《迷戀記》、《此生》這兩本讀書隨筆讓我捧讀玩味,那篇《沈從文與20世紀中國》的長文我也曾拜讀數遍,扎實細密的論述中滲透了對沈從文其文其人在動蕩非常時期掙扎思索的無言敬意與慨嘆。如今,張新穎“十六年磨一劍”的著作《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得見天光,我借著這個機會終于見了他本人。 酷暑難耐,下午我來到北京貝貝特公司所在的化工大院,七拐八繞之后,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拐角的幽靜院落。這里冷氣開得很足,綠植種得很美,小院布置得素凈雅致,兩排木椅木桌非常認命地躲在院落一側,我卻因為炎熱,都顧不得欣賞一下門廳里擺放的各式手工藝品,就鉆進屋子里找沙發坐下。等了一小會兒,張新穎來了。我猛地一抬頭,看見一個個子不高、戴著眼鏡、正小喘氣兒的中年人,他的右臉頰有一顆黑痣,嘴邊掛著淺淺笑意,透過鏡片可見瞇起的眼睛里溢滿了安詳平和,見狀如此,我略有緊張的心也松弛下來,我知道,從《沈從文的后半生》這本書聊起,我還可以與張老師扯得更遠一點。 ▲張新穎教授 新京報記者 秦斌 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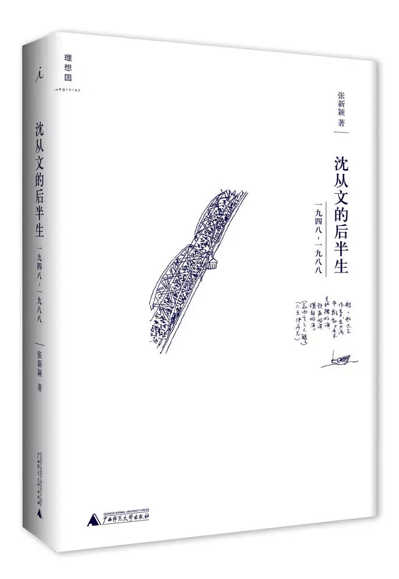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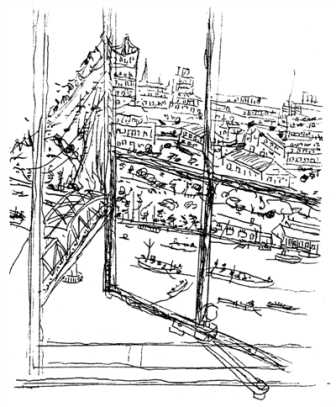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5-08-23 08:38:57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